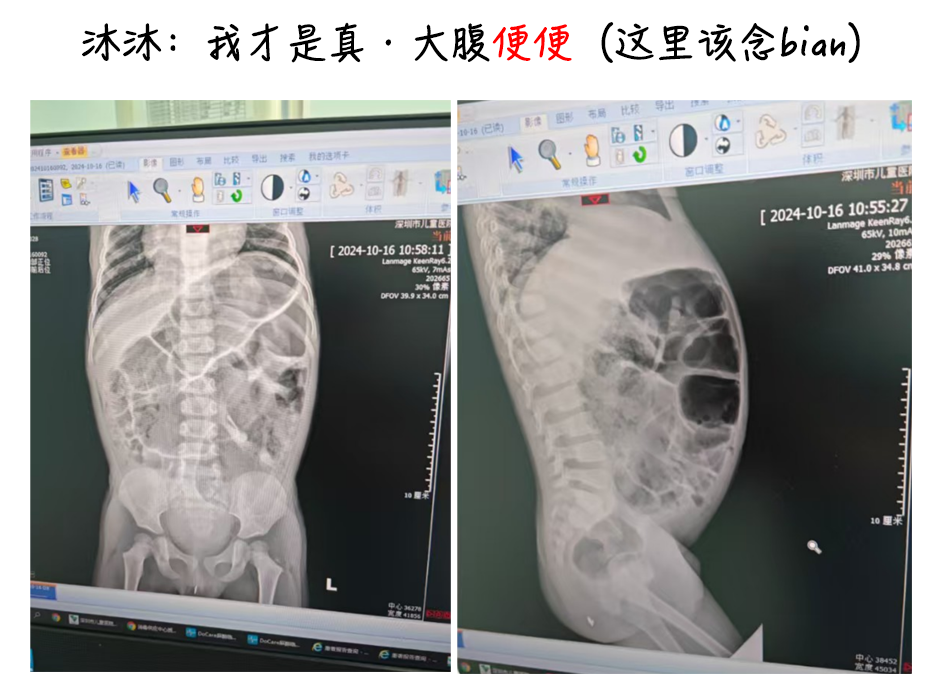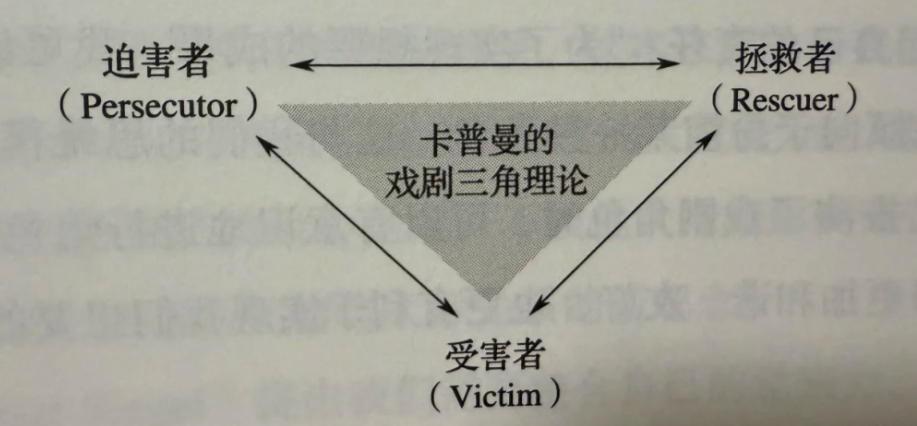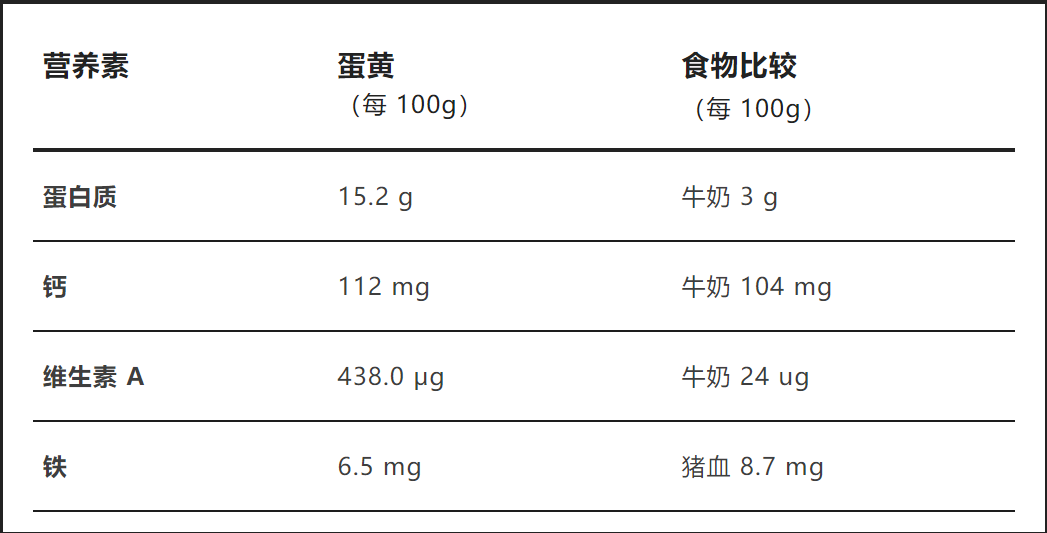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很多人被这样对待却没意识到……
你或许听说过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实验”:如果对一杯水说赞美的话,它冻结后会形成形状美丽的冰晶;而如果不断对它进行辱骂和贬低,冰晶的结构则会变得混乱、丑陋。尽管这一实验后来被证实缺乏科学依据,属于伪科学范畴,但它所反映出的社会心理却值得关注——人们愿意相信,语言具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
长期遭受言语打压
会影响大脑认知
· 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海马体体积平均减少约 12%~15%,且缩小程度与抑郁持续时间呈正相关。
· PTSD 患者(经历过战斗经历、童年创伤)的海马体体积减少达 8–26%,受损程度同样与创伤经历的持续时间显著相关。
·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非情绪性疾病中,也能观察到相似现象。单纯由于身体分泌过多皮质醇的库欣综合征(Cushing’s Syndrome)患者中也能观察到双侧海马体萎缩,认知能力下降的现象。并且这部分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海马体体积可部分恢复。
· 注意力难以集中:持续应激状态下,个体往往会出现注意力分散、信息过滤能力下降;
· 计划能力下降:前额叶的执行功能受损,使人难以完成多步骤任务或有效制定目标;
· 冲动控制减弱:压力会削弱行为抑制系统,增加冲动行为、冒险决策或情绪爆发的风险;
· 情绪调节失衡:前额叶皮层原本是杏仁核的“刹车片”,但在慢性压力下,这一平衡被打破,负面情绪更容易持续。
长期被否定
容易造成习得性无助
“变笨了”,不一定等于智商下降
脑部外伤:如严重车祸、摔落等造成颅脑损伤,可能损害额叶、颞叶等关键区域,影响推理、记忆、执行功能。
中风:尤其是影响语言、注意或空间加工相关脑区的梗塞或出血,可导致局部性或广泛性认知功能丧失。
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随着神经元逐渐退化,智力水平随病程进展而下降。
严重感染:如脑炎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可能造成海马体或额叶永久性损伤。
慢性酒精中毒:长期酗酒会造成脑萎缩,尤其影响前额叶与小脑的结构和功能,进而损害认知效率。
早期创伤与剥夺环境(如极端贫困、忽视、虐待)会干扰神经发育关键期,造成神经网络结构异常,从而限制智力发展。尽管这种影响多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但其后果可能持续至成年,表现为 IQ 分数显著低于正常发育轨迹。
重度抑郁症、广泛性焦虑障碍、双相障碍等常伴随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处理速度下降,影响学习与决策效率。临床上称之为“认知功能障碍(Cognitive Dysfunction)”,部分患者在疾病缓解后可见一定程度的认知恢复。
慢性应激状态下,高水平的皮质醇会对海马体、前额叶皮层等关键认知区域产生毒性影响,损害记忆、情绪调节与决策能力。
经常被否定,可以怎样做?
· 学会区分“评价”与“事实”:比如“这件事不应该这样做”并不等于“你很差”。把行为和自我价值拆开看,是修复内在认知的重要一步。
· 觉察内在批评:当你发现自己习惯性地使用否定性语言(如“我太差了”、“我做不到”),可以尝试用更温和、中性的表达替代,如“我现在还不熟练,但可以慢慢练习”。
· 练习自我肯定与情绪表达:每天给予自己一点积极反馈,如“我今天完成了任务”、“我有在努力”;同时学会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压抑或否认。
· 调整社交环境:尽量减少与频繁贬低、否定你的人接触,增加那些能给予你支持、尊重和理解的人际关系。
· 专注可控的“小事”:从微小而具体的任务开始,比如整理房间、完成一段短跑、认真吃完一顿饭。建立对环境的掌控感,有助于打破“我做不到”的思维模式。
· 设定阶段性、可实现的小目标:例如“本周完成两次运动”“每天写 3 分钟情绪日记”,并记录达成过程。这些正向反馈能逐步重建自我效能感。
· 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情绪状态长期低落、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出现“失控感”,请及时寻求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科学的治疗和干预能有效缓解压力对大脑造成的损伤。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