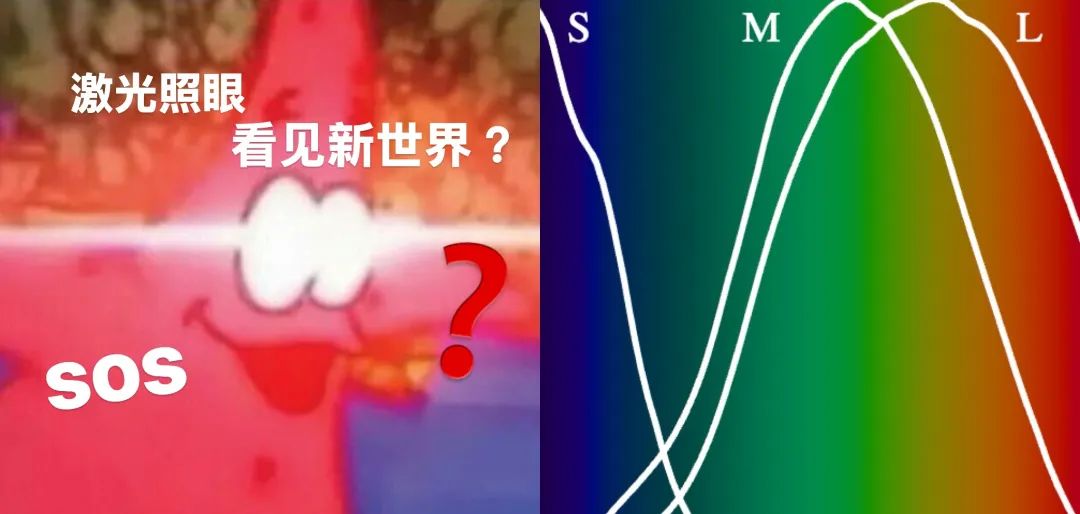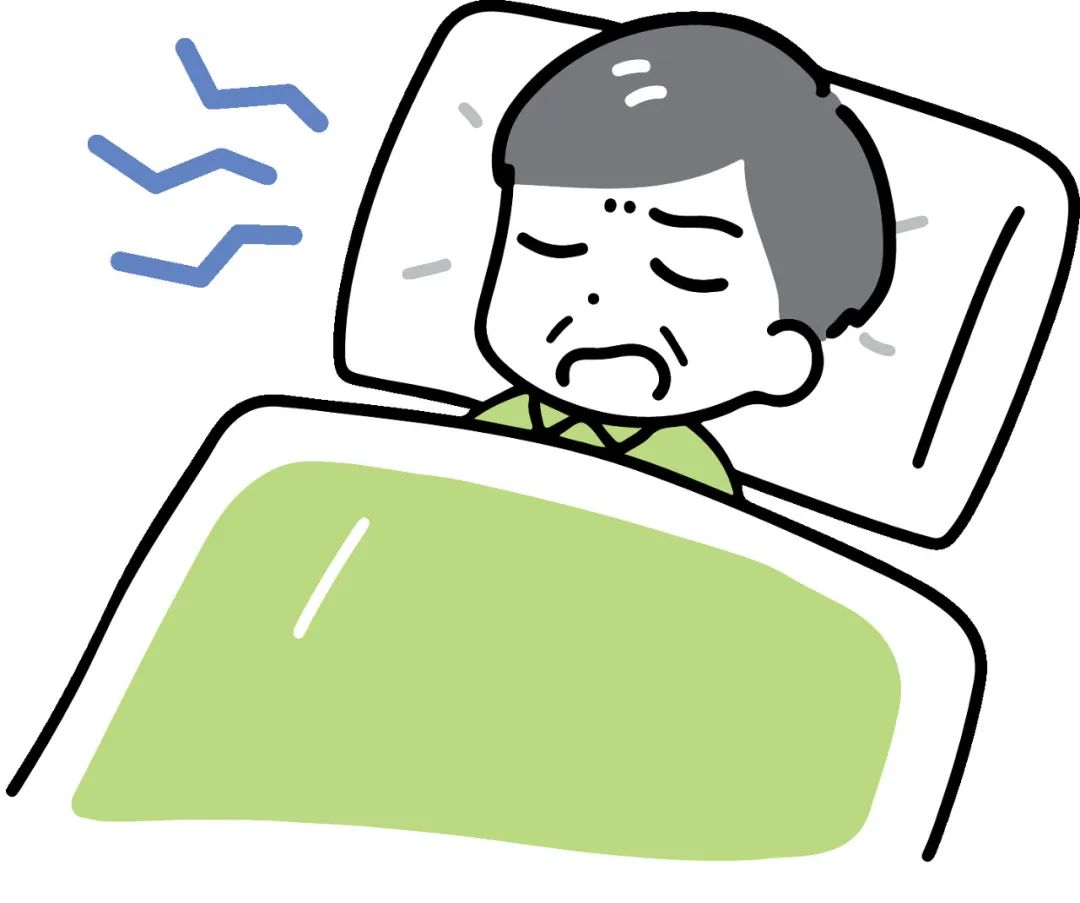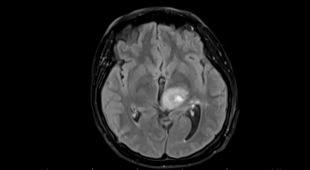剺面 “谁也没料到,今年的风沙竟比原来要严重得多!”
法信伸手拿起书,瞧见封面上三个大字《占灯法》,又有小字“唐李淳风著”,便说:“是本算命的。”
一
游方僧悟空在于阗城入定修闭口禅,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已有二十个月。
这时的于阗城还是从敦煌到西域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往返丝路的商旅们带来中原的瓷器和远方的宝石,把这座孤悬于大漠中的古城映得珠光熠熠。但这些都与悟空无关,他的皮肤干枯如积年的老树,难有半点凡俗挂绕。
没有人能说清悟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于阗的,只知道他在这无亲无故的地方收了一名叫作“法信”的徒弟,这是个伶俐的和尚,每天开门扫洒、焚香念佛、伺候师父,一年到头绝无懈怠,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和尚。
这天五更刚过,城门已开,陆续便有商队进出。法信做完早课,正于门前扫洒,忽听得远处“达卜”鼓响,知是城里又来了卖艺的。他悄悄掩了房门,瞒着师父想去瞧热闹。
法信来到街上,人群早把街边空地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个踮着脚往里瞧,里面夹着呼呼棍梢破风声。法信正欲看时,人群里忽然一声娇喝,那棍花舞得越发急切,恍惚间风雷震动,众人悚然,又齐叫一声好。
法信挤进人群,这才瞧见那使棍的原来是个劲装束发女子,一旁搭伙的卖艺人将达卜鼓擂得震天响,那女子应着鼓声,脚下闪转腾挪,手中哨棍飞舞,使到妙处,只觉人如皎月,棍若流星。
法信一看,认的是熟人,忙道:“车禅儿,你又来了!”
那劲装女子听见,朝他一笑,手上却无半点迟滞,三通鼓后,堪堪将整套棍法使毕,这才将棍一掣,后退几步,朝周围行个团揖,众人欢声雷动,赏钱如雨点抛进箩中。
车禅儿才要说话,忽见街上几人策马疾驰而过,为首的锦袍官员朗声提醒随从莫要冲撞行人。有眼尖的瞧见,便高喊起来:“是郑大人!”
听说是郑大人,正围观卖艺的众人便都欢喜,四下鼓掌雀跃,那郑大人虽然面有疲色,却笑呵呵地招手回应,一边带着随从策马往城西门去了。有知道内情的,说有西域商人欲在城外驻扎,郑大人便是去裁决此事。
法信知道,这郑大人单名一个据,是朝廷钦命的于阗镇守使。人们都称赞他行事端谨,也正是在他多年治理下,于阗城才能固若金汤。近年来西域虽乱,却始终无人敢来觊觎此城,得保敦煌以西太平。
车禅儿瞧着郑大人的背影,一双眼亮了起来。不等人群散开,她便拉住法信的手说道:“小和尚,咱们且去瞧瞧。”法信还惦记着师父悟空,想赶紧回去,可车禅儿哪由得他?
“等回来,我替你向师父求情!”
这车禅儿生性好动,早些日子来于阗城卖艺的时候,听说法信的师父悟空在修闭口禅,当时就找上门来拜访,法信费了好大劲才拦下这个光鲜活泼的女子。
两人撇下大伙,来到西城门边,早被戒严的兵士拦住,不许他们靠近。原来城外候着十余名胡商,郑据亲自出城与他们相谈,自然戒备森严。车禅儿见出城无望,就想登上城楼去看,自然又被拦下,当时就哭了出来。
法信不忍见她泫然泪下,忙扯住她的衣袖,悄悄带她跑回自己住处——原来法信和师父悟空所住的木屋就建在于阗城西门边一座废弃的烽燧上,仗着地势高,木屋的楼顶便紧挨着城墙的一座望台。
法信带着车禅儿来到房边,两人都身形瘦削,毫不费力便攀上了低矮的屋顶。法信正要带着车禅儿折身翻上城墙望台,车禅儿便透过阁楼的窗口,瞧见昏暗的阁楼里盘腿垂首坐着个一动不动的老和尚,她大感好奇,忙拉着法信的衣袖,小声问道:“那是你师父?”
法信一回头,也瞧见师父正盘腿打坐,忙朝车禅儿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赶紧翻上望台,把车禅儿也拉了上去。这座望台白天少有人在,法信带着车禅儿偷偷摸到墙边,探头看着下面正在谈判的郑据和胡商。
“你可要小心,千万别让我师父发现,不然我就惨了。”法信紧张兮兮地再三叮嘱道。
“你怎么这么怕你师父?之前我想登门拜访,你都不许。”车禅儿俯在墙边往下看,嘴里还在抱怨道。
“我都说了,师父在修闭口禅,不见一切外客。之前郑大人要见都没让呢!”法信小声解释道。
“好了,不让便不让,你别耽误我正事。”车禅儿被他絮叨得生厌,嘟嘴抱怨道。法信忙住了口,车禅儿探身看着下面的郑据。
城门下,那群胡商中为首的正跟郑据飞快地说着些什么,郑据先是摇头,但那胡商随即捧出一团光灿灿的物事,奉到郑据面前。
“那是什么?”车禅儿被那光灿灿的物事晃住眼睛,惊问道。
看来郑据也对那东西颇好奇,接过翻来覆去赏玩。法信居高临下仔细一瞧,却见那东西原来是件通体剔透的带棱圆盏,随着郑据来回转动,阳光穿过其中,在四周荡漾开迷离的眩光,显得宝气非凡。片刻之后,郑据终于点了点头,众胡商喜不自胜,纷纷额手相庆,接着就纷纷告辞。
等那些胡商走远,郑据等人才策马回城。法信和车禅儿不敢在城墙上久待,忙沿原路回到城中,便听见人人奔走相告,说有胡商从天竺习得“玻琉璃”器皿的烧制之法,想在于阗城外筑造土炉生产,希望城里能每日供给他们水和柴火,他们则用生产的玻琉璃器来交换。
于阗城人人都知道“玻琉璃”是天竺奇珍,其质坚硬,却又能透光如水,是丝路上最上等的器物,据说随便一件就价值连城。眼下传出这样的消息,谁能不动心呢?法信和车禅儿曾亲眼见到那件宝贝,自是深信不疑,但翻于阗城墙偷看这事,两人谁敢说出去?当日只得各自散了。回到住处,法信在师父身前点燃一盏香油灯,自去打坐念经不提。
当天夜里,于阗城内忽然明火执仗,人声喧哗。有胆子大的逾墙偷看,却见街道上满是巡逻的兵士,个个万分紧张。第二天便有消息传出:于阗镇守使郑据夜间遇袭,刺客逃之夭夭。
一时间,城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说郑据负伤垂死,也有说刺客是城外胡人派的,还有说郑据的亲随拼死搏斗,已将刺客重伤。
法信听到这消息,登时疯了一样满城找车禅儿的下落,果然四下里遍寻不见。他这才恍然大悟,忙折身回到自己住处,登上阁楼去瞧,悟空仍然在里面盘腿打坐,透过窗口,正巧看到车禅儿从望台的缝隙里探头看他。
法信跳出窗子,翻上望台,这才发现车禅儿缩在望台内部的架梁上,这里平日巡逻的人路过都得低头,很难发现她的影踪。车禅儿见到是法信,忙招手让他上来,法信见她鬓发纷乱,脸上没有血色,显然伤得不轻。
“是你?你为什么要刺杀郑大人?”
“你难道就是来问这个的?”车禅儿恨道。
法信双手合十念佛:“罪过罪过。若不是郑大人,只怕这城早就失守,生灵涂炭,岂不是罪过。”
车禅儿咬着牙说道:“可他杀了我祖父车奉朝。”
“啊?这从何说起?”法信惊道。
“我祖父年轻时立志遍览天下风土,他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件,就自于阗城中发出,信上说受到镇守使郑据挽留,之后便下落不明。”车禅儿眼里闪着光芒:“你说,这仇我该找谁?”
“所以你三番五次来于阗——”
“你说呢?”
“我还以为你——”法信双手合十,喜道:“谢天谢地。”
车禅儿脸一红,没再接下去。半晌,她才推了推法信的手臂,说道:“这些天我躲在这里养伤,你不必时时来找我,等平静一些,我自会离去。”
法信这才松了一口气:“你不再寻仇了?”
“我说出祖父的名字,郑据竟让随从放我逃走。”车禅儿捂着伤口皱眉道:“我觉得仇敌另有其人……”
“那就好,我把吃喝藏到阁楼外面,你若是需要,只管来拿。”法信说罢,匆匆自去了。
又过了几天,法信竟真的没去找过车禅儿,每日照顾师父、烧香礼佛不提。只有每天瞧见藏起的食水不见,他才放下心来。而郑据也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特意骑着马穿城而过,居民们见到他安全无虞,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城内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过了大约十多天,城里面忽然又人人惊动。原来是把守城门的兵士发现,那些胡商在城外垒起几排数米高的土炉。那些炉子比人们原本预料的大得多,也多得多。炉子四周堆满如山的薪柴,烈火在炉中猛烈燃烧,汇聚在一起的滚滚黑烟如同冲天而起的巨龙。
随后烟柱在沙漠边缘吹来的风中倾倒,不偏不倚地砸向于阗城。
二
谁也没料到,今年的风沙竟比原来要严重得多,再加上漫天飘扬的烟灰,把整个于阗城都淹没在令人窒息的昏沉之中。即使相隔数里,城墙上、房檐上、街道上都落满了这些黏稠的黑灰,无论怎么擦洗都是徒劳。不少人都开始咳嗽,他们就着烟灰吃下刚烤好的馕,把胃壁都熏黑了。
这时人们才知道,胡商用玻琉璃器交换清水和柴火的消息越传越离谱,说是只要送水和柴火去城外胡商的驻地,就能获赠一件玻琉璃器皿,这下城里人人轰动,很快,狡黠的丝路商人们最先回过神来,立刻在城中大举收购余柴,又买水一起送往胡商处去。果然,他们带回了数量众多的玻琉璃器皿,并准备以西域奇珍的名义沿丝路贩卖。这下城里谁不动心?
城中的居民也乐得将家中的余柴鬻给那些胡商,不少家无余柴的人甚至专程去附近绿洲砍树、挑水,用来和胡商交易那些精美的玻琉璃器皿,一时间人人都以拥有这些晶莹剔透的玻琉璃器为荣。
他们将附近绿洲的树全都砍光,失去了树木的绿洲很快沙化干涸,终于在大漠日复一日的风沙中消失殆尽。
现在只剩下大漠中孤独屹立的于阗城。郑据立在城门上,面对着城外滚滚的浓烟发愁,他先是叫城里的人停止每日供应的水和柴火,随后又派人出城,叱责那些胡商。
没过多久,那个胡商首领就在使者的带领下匆匆赶进城中,乞求郑据开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胡商首领答应每日只开一半炉子,一旦遇到上风便不可开炉,城中则统一供给定量水和柴火,禁止再私下交易。
又过几天,这些胡商果然都依例每日只开一半炉子,烟尘便不再像之前那样呛人,城里的人便都略微放松下来。
这些天城外炉火事件沸沸扬扬,法信发现自己放在阁楼外的食水上落了厚厚一层烟灰,不由得担心起车禅儿的安危来。他几次偷偷登上望台去找车禅儿,却始终没见到她。想必她这次真的走了。
法信缩在车禅儿藏身的地方,发现也是厚厚一层烟灰。他探头看着城外的风景,原来这里正巧对着城外胡商筑造的土炉,被风一吹,烟灰全都灌进瞭望台里来,难怪车禅儿不愿在这多待。
想起车禅儿,法信怔怔地望着城外的土炉出神,只见那些炉子只有一半点着火,闪烁的火光散落在林立的土炉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就像是雅丹魔城里诱人身陷其中的冥火。
法信的头忽然没来由地疼起来——他的脑海里忽然浮出那个由燃烧的炉火组成的形状。
虽然不认识,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那是一个符号,这让他没来由地恐惧起来。
“你说什么?”由于重伤未愈,郑据的脸色并不好看,但是他听到法信这个小和尚带来的消息时,还是情不自禁地撑起身子。
“城外胡商的土炉在向城里传递消息。”法信紧张地说道。
“什么信息,向谁传递?”郑据身边的幕僚们带着讥讽说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见过这些符号!”法信越是拼命回想,越觉得头疼欲裂。
“哈哈哈哈,这小和尚,怕是读经读傻了。”那些幕僚哈哈大笑起来:“城外的胡商总共才几十人,就凭他们能干得了什么?烧个炉子能传递什么信息?”
“你们——我——” 法信越发焦躁起来,头也疼得越来越厉害。一种莫名的危机感让他恨不得将自己的脸撕开,他总觉得自己若是解不开这些谜题,那整个于阗城都将生灵涂炭。
“你是悟空收的那个小徒弟?”一直没说话的郑据突然问道。
“是,弟子名为法信。”法信面对这个放过车禅儿的男人倒很是放松。
“法信……嗯,你师父悟空,年轻时立志追随玄奘足迹,求学于天竺,熟知当地种种数术之法,是个很有见识的、有大慈悲心的人。你既是他的弟子,知道这些也不奇怪。”郑据微笑着说道:“但我身为一城之主,不能凭你一面之词作出决断”。
“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去找你师父,看看这些信息的出处究竟在哪,如果能证实确实是在传递信息,这头功便是你的。”
法信顶着风急急忙忙跑回住处,开始翻箱倒柜,到处都是师父从各地收集来的东西,其中尤以天竺带回的经书为主,可是法信几乎都看不懂,面对着一本本无字天书,他简直快要发疯。
他一定曾经看过这些符号,而且他相信,只要他再次看到,一定会认出那些符号来,可是他不吃不喝不眠,翻找了整整一日一夜,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也没有找到任何对应的文本。
他急得快要发疯,全城居民的性命都掌握在他自己手上,可是他连给师父点上每日惯例的香油灯的时间都没有。
一想到还没给师父点上香油灯,他终于崩溃到大哭起来,不由分说冲上了师父修闭口禅的阁楼。阁楼内,悟空仍然盘腿坐在那里,见到师父饱经沧桑的面容,法信噗通一声跪倒在师父面前,磕头道:“师父,请为弟子指点迷津。”
悟空盘腿坐着,并不答应。法信一想到满城居民,郑据,还有车禅儿的性命,不由心如刀绞,一边说着事情来由,一边磕头如捣蒜,将地板撞得直响。
法信的眼睛被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迷离,可悟空始终一动不动,仿佛这座城市的安危与他丝毫无关。
法信急火攻心,突然跳起身大叫道:“师父,弟子愿以一人性命,换全城百姓性命!请师父开示!”
说罢,他跳起身,一头重重磕在地上,当场昏死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又一天深夜。他感到自己的头脑无比清明,于是挣扎着爬起,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抬头看向师父悟空。
可是他的希望还是落空了,悟空仍然绝情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师父!”法信悲愤地叫道,这次他的眼泪混着血水一起模糊了双眼。
然而就在他绝望之际,忽然发现悟空双手竟然做了一个“合十印”。
师父之前是这个动作吗?法信头脑里一阵混乱,但是这个手势马上让他感到无比熟悉——他的视线越过盘腿而坐的师父头顶,落在了师父身后墙壁上悬挂着的佛像图上。那是一张有关《十地经》的图画,画中的佛像正同样姿势,双手合十——再看悟空时,原来并没有动。
法信仿佛受到了某种冥冥中的指引,他情不自禁地扑过去,靠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仔细查看挂画上的图案。果然,就在佛像四周,围绕佛像的十个圆环中,其中一个赫然写着与那点燃的土炉相对应的符号。
圆环里写着“4”,下面用汉字标着“此为天竺数字四,即善心”。
“就是这个!”法信按捺住内心的狂喜,把这个符号的形状记下,又连忙去把周围的符号都看了一遍。
“何等为十? 一直心,二柔软心,三调柔心,四善心,五寂灭心,六真心,七不杂心,八不烯望心,九胜心,十大心。”
法信这才明白,原来图上十个圆环里写的是对应汉字一到十的十个天竺符号。
图上的“4”,对应的是《十地经》中的善心。那么胡商点燃的炉火,传出的“4”所对应的又是什么信息?
想到这里,法信急中生智,连忙翻窗出了阁楼——他想亲眼看到那些胡商今天用炉火传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黑暗中,跳动的火光组成了天竺数字7。
当他探头探脑地从望台上往外看,想知道这个7代表什么的时候,一只白嫩的手掌从旁边伸出,牵住了他的衣领。
“你的头怎么破了?”
法信转过脸去,在黑暗里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车禅儿。
他哇地一声大叫起来,车禅儿慌忙捂住他的嘴,嗔怒道:“仔细把巡逻的兵士招来!”
可是车禅儿自己反被法信紧紧搂在了怀里,法信颤抖着在她耳边说道:“禅儿,我好想你。”
车禅儿顿时红了脸。
“什么,你想去胡商的营地刺探?” 车禅儿坐在月光下的望台里,她的脸色比之前好了许多,但当她说出来自己的计划时,法信还是被吓了一跳。
车禅儿倒是波澜不惊,她点头说道:“之前误伤郑大人,这些天我始终不安。刚才你说胡商似乎有所图谋,不如咱们这便去探个究竟,也能将功赎罪了。”
法信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真要去,我一个人去便是。怎能牵连了你?”
车禅儿笑道:“之前私藏刺客的时候,怎么不怕我牵连了你?”
法信无话可说,两人翻越城墙,趁着无边夜色向几里外的胡商营地走去,一路只觉夜风拂面,于路无话。
三
来到胡商营地旁边,果然见营地里戒备森严,剑拔弩张,完全不像寻常商人作为。车禅儿习武出身,自不必说,那法信也算得上身手灵活,借着风声呼啸,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巡逻的哨戒,进了胡商营地里面。
两人的注意力很快被最大的那顶帐篷吸引过去——夜色里除了营地中间的篝火,其余帐篷里都是漆黑一片,鼾声如雷,唯独最大的那座帐篷里亮着灯,里面影影绰绰,不知其中深浅。
车禅儿带着法信绕到帐篷后面,偷偷掀起篷角窥视其中,却见帐篷里空无一人,当中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盏油灯,灯旁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卷。车禅儿瞧那油灯已经烧得半干,几寸长的灯花都已经蜷曲起来,显然许久无人打理,于是打了一个手势,和法信一起钻进帐篷里面。
钻进帐篷,外面的风声顿时小了许多。车禅儿一指桌上书册道:“那是什么?”
法信伸手拿起书,瞧见封面上三个大字《占灯法》,又有小字“唐李淳风著”,便说:“是本算命的。”
“再去别处瞧瞧。”车禅儿见这帐篷虽大,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便招手要走。恰在此时,只听得帐篷外一声呼哨,接着便是十几柄长枪捅穿帐篷,直刺向帐中二人,法信只觉劲风扑面,几道明晃晃的枪尖已经直刺面门。
“有埋伏!”车禅儿眼疾手快,拔出背上哨棍,一个进枪式,先将攒刺来的枪头拨开,拉住法信的手,一起朝外冲去。
两人还未出得帐篷,便又听见箭矢破空声音,这下车禅儿也不得不放开法信,双手将棍舞定,一连拨开两三支长箭,但这一停顿,就和法信前后错开。帐篷外早伏下四五名大汉,一起来捉二人。车禅儿挥棍力敌数人,再回头便不见了法信踪影,见势不协,车禅儿只得且战且退,趁乱逃出营地去了。
这边法信刚出帐篷,还没来得及跟上车禅儿的进退,早被人拿住双腿扯翻在地,另一人拔出明晃晃的短刀就朝他面门刺来。他见状大惊,正待挣扎,忽然有人用胡语叫道:“住手,是突昏!”
法信还稀里糊涂,还没意识到自己竟能听懂胡语,便被人从地上拉扯起来,推到篝火前。却见那些伏击自己的人都围拢过来,为首的正是那天与郑据谈判的胡商首领。
“哈哈,突昏,我还当你胆子小,临阵逃走了呢!”那胡商首领大笑起来,狠狠拍了拍法信的肩膀。
“呃……啊……”法信一时间不知道他在说谁,也不知道要怎么说胡语。
“没想到你在于阗城里潜伏下来,还打扮成这副和尚样子。”那首领满意地笑道:“他们要我不再等你,我却知道,你看到炉火发出的消息,就一定会回应。没想到,你竟然冒冒失失地大半夜闯回来。”
“你……叫我什么……”法信惊愕地看着他,一张嘴,说出的却是结结巴巴的胡语。
“和尚当太久,连名字都忘了?”胡商首领揶揄道,周围人齐声大笑起来:“你叫突昏,别再忘了!”
“我叫法——我,我——”法信刚要报出姓名,可是却没法用胡语说出法信二字来。
“当初你说要入城侦查,没想到一去就是一年。我也不知你下落,只得按约定,将每天占灯结果,通过火光传入城中,只等你看见,按计划行事。”
“什么计划?”法信更是摸不着头脑。
“你怎么回事,脑子坏了?”见法信一问三不知,首领顿时恼火起来,看着他的眼神也逐渐变得狐疑。
“不,我是说,怎么一直没见你们动作。害我在城里等了那么久?”法信见周围人虎视眈眈的样子,知道他们认错了人,便急中生智,将计就计道:“你们若是自行动手,计划早就成功了。”
“风向一直不对。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必须等西风来,才能把烟尘送进于阗城里,还必须有风沙才行。”首领恨恨地说道:“之前虽然有次西风,但却没有风沙,倒惹得于阗城里的人十分抱怨。”
“风沙和烟尘进城之后要怎么办,还记得吗?”法信索性佯装到底,用反问的语气说道。
“记得,大伙都记得。”首领和周围的人都说道:“便用生产的玻琉璃器,将附近阳光全部聚到沙尘上,那便可以如愿了。”
法信听了一惊,正要问这能如什么愿,却被首领粗暴地挥手打断。首领对他说道:“你好不容易在城中潜伏下来,正有许多事情要做。以后断不可亲自出城,更不要如今日这般,还带个女娃同来察看暗号,险些走漏我们机密。”
说着,胡商首领一推法信,喝令道:“快回城去,切莫被人发现。”
法信本以为自己今日势必要丧命在这胡商营地中,却没想到反从对方口中打探出许多重要信息来,他正想着刚才胡商首领所说约定暗号是什么,接着就被糊里糊涂地推出了营地,重新走在了回城的路上。
他忽然觉得心里放松了许多,脚步也变得轻浮起来。
“赶快回城里去,将这些报告给郑大人!”法信这么想着,忽然头后重重挨了一闷棍,仆地便倒。
他昏迷前挣扎着转过脸来,对上车禅儿半是愤怒、半是难以置信的眼神。
法信挣扎着醒过来,已经又是天亮。他的头被车禅儿打得很重,鲜血都已经干结在他光头上。
意识到自己没死,法信这才难以置信地爬起身来,他的头很疼,像是从里面裂开,但是总算还记得要把讯息传回于阗城的事情。于是他撕开僧衣包住头,脚步踉跄地往城里赶。
他进了城门,打算回住处换掉血衣,再赶去见郑据。没想到他刚进屋门,立刻被人从背后一脚踹倒在地,他大惊失色,正要爬起,却被人一脚踏在光头上。
“抓住他了!”打翻并抓住法信的是两名兵士,跟在他们后面走进屋来的,却是郑据和车禅儿。
他们看向法信的眼神里满是愤怒。
“放开我,我有话要说!”法信挣扎着大叫。
“没想到你竟然是胡人的探子!”郑据冷哼一声,指着旁边的车禅儿:“幸好有她听见,不然我们都被你蒙骗了。”
“我不是,我是——”法信还没说完,就被按住他的兵士堵住了嘴巴。
“哼,没想到就连悟空法师也被你骗过了。”郑据说着,迈步走上楼去:“我要告诉他,他老眼昏花,竟收了这么一个好徒弟。”
法信绝望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他挣扎着看向站在旁边不说话的车禅儿,可车禅儿只是轻蔑地瞪着他。
郑据走上楼去,只过了短短片刻,忽然听得楼上一阵“咚咚”闷响,紧接着就看见郑据连滚带爬地从狭窄的楼梯上摔了下来。
“大人!”原本按住法信的兵士忙上前搀扶,可郑据却状若疯虎,挥手打开他们,一把抓住倒在地上的法信脖子,将他从地上拎起。
然后一个接一个耳光狠狠地抽在他脸上。
“你这狼心狗肺败坏人伦猪狗不若丧尽天良的东西!”郑据两眼血红,打一巴掌,便骂一句。
他那样子实在太过吓人,就连旁边的兵士和车禅儿都吓得退开,看着郑据一巴掌一巴掌结结实实抽在法信脸上,把他打得不住晕过去又苏醒,吐牙齿如吐石榴籽。
郑据打了近百下,这才恨恨地将满脸血肿的法信往楼梯上拖去,法信的头砰砰地撞着楼梯,被他一路拖上了阁楼。
“看看你做的!”郑据指着阁楼里那地狱般的情景,恶狠狠地咆哮道。
法信原本还被打得耳鸣不止,可看到阁楼里的情景时,只觉得好一似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顶梁骨都从中裂开一般。
他的师父悟空依然保持着盘腿坐的姿势,只是整个人僵硬地向后倒下,仰面朝天,一动不动。
郑据红着眼走过去,伸手掏开悟空的僧袍和他的肚子——那是一道很久以前留下的伤口,早已干枯的伤口自颈至胯下,几乎将他整个人撕开。
悟空的肚子里是一尊体态庄严的佛像,它深邃的神情透过悟空的肚子,看着阁楼里的众人。
直到车禅儿失控的尖叫声响起,所有人才从这幅地狱般的惨状里回过神来。
在这声尖叫里,法信终于回想起了一切。
怎样趁着夜色翻进于阗城,怎样惊动兵士而不得不潜藏进这座破屋里,怎样翻检书信、发现一个不仅仅是攻下于阗城的重大机密,怎样被老和尚发现,自己怎样杀人灭口,又是怎样收拾案发现场……随后发生的一切,其血腥程度就连“法信”自己都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
四
看到那个佛像,他终于想起来悟空是怎么才能保持这样的坐姿整整二十个月不动的。但也正是靠着这个佛像和一个关于闭口禅的拙劣借口,一场血腥的凶杀案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他把很多东西,包括因为极度血腥的场景而深受刺激的记忆一起埋藏在了那天的阁楼上。悟空法师的弟子“法信”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于阗城里坦然现身。
现在那个记忆正从“师父”的肚子里窥视自己,“法信”觉得自己也被从中剖开,露出皮相下血淋淋的真容来。
“噢噢噢噢噢——”“法信”被堵着嘴,却发出撕心裂肺的狂叫。
“把他关进死囚!传我的命令,关闭所有城门,提防胡人来袭!”郑据大叫着发泄狂怒。
被他一脚踢翻在地的“法信”看到“师父”所坐的蒲团下面,露出一本《占灯法》来。
“灯,乃一家照鉴之主。开花结蕊,吐焰喷光,可知人事之吉凶,可占天时之晴雨,仔细观翫,皆有验事。凡灯有花,任其自然开谢,不可剪弃吹灭。如此,则反能为灾。灯三吹不灭,更不可再吹,切宜戒之。”
“法信”倒在铺着破败稻草的死囚牢里,全身鲜血淋漓,嘴里喃喃念着《占灯法》的内容。
随着他的真实面目暴露,他也终于想起来这些东西来。
“若旱多时忽灯焰红花。短小而频频点滴者。则三日内有雨。
若天阴日久。忽灯结红花光彩明莹者。来日晴。
灯若黑烟上起。红焰下垂昏者。主来日雨。
灯若无烟但红焰左右摇曳不定。主来日有大风。
灯焰向东指,来日有东风。
灯西指有西风。
南指有南风。
北指有北风。
灯红焰短昏频垂点不止。主来日有雨。若夜夜如此。必见连阴。
灯若见红焰光而长明、不动摇者。则必晴明。”
一共十条,每一条都对应着一个数字,也对应着一个气象。那一天他看到的是四,也就是“来日有大风”,第二天果然如此。他和车禅儿闯入胡商营地时,也遇到了如第七条所说那样的南风。
一想到车禅儿,他的心就绞痛起来。
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可却无法将一切都向她全盘托出。
他知道一旦等到西风和大风沙的日子,整个于阗城都完了。
就在他绝望地用头狠狠碰着牢笼的时候,车禅儿竟然真的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俯视着他。
“车禅儿……”“法信”挣扎着开口,嗓子却干哑得几乎出不了声。
“郑大人都告诉我了。”车禅儿冷冰冰地说道:“悟空就是我祖父车奉朝。”
这消息仿佛当头一棒,顿时把“法信”打蒙了。
车禅儿带着冷笑继续说道:“当初祖父要回中原去,受郑大人挽留才待在于阗,没想到竟被你杀了。”
“法信”挣扎着跪起身,接着砰砰砰砰地不停把头往地上撞,像是请求车禅儿原谅。
“我不会原谅你的……想也别想……我都没见过祖父……你为什么……”车禅儿哽咽起来。
“法信”突然抬起头来,挣扎着指向牢笼外的一盏油灯,那灯的灯花虬结着,垂向西边,上方摇曳的红焰左右摇摆不定。
车禅儿惊讶地看着“法信”的举动,她满是阴云的脸上忽然有些松动:“你想做什么?那灯怎么了?”
“告诉郑据,那些胡人要来了!”“法信”用几乎掉光牙的口齿挣扎着说道。
车禅儿看看灯,看看“法信”,似乎想起当初在胡人帐篷里时的情景。她显然意识到了什么,低头对“法信”小声说道:“这是你们的暗号?”
“快——”
“法信”还没说完,只听天空之上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那是西风的呼啸。
此时的于阗城正被笼罩在来势汹汹的西风中,由于城外绿洲先后消失,此时弥漫的风沙让整个天地都昏暗下来。
而那些胡商则同时点燃起所有的土炉,数十道未曾燃尽的烟尘冲天而起,卷裹在风沙里,黑压压地笼罩在整座于阗城上空。
郑据正全副戎装,带着部众挺立在城墙上,眼望着这令人绝望的末世像。
“郑大人!”郑据闻声转过头,看到车禅儿用衣角蒙着脸,顶着风沙艰难地走到城上。
“怎么了?”
“法信——那个家伙招了,他说对方打算利用西风将烟尘送进城里,之后用玻琉璃器聚光引火,就能利用这些和风沙混在一起的烟尘引发爆炸,炸毁城墙!”
“什么?”郑据大惊失色:“这谁能挡下风来?”
“大人,或许可以效仿古人,在城中大量点火,令风转向!”旁边的幕僚建议道。
“笨蛋,你自己点着火,都省得对方动手了!”车禅儿破口大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全城的人备上足量的水,四下泼洒,让烟尘尽快落下来,才能让它们不至于聚集起来,这样便不会引发爆炸!这是那家伙说的!”
“城里哪还有水!之前全让他们送给胡人去了!”郑据愤怒地敲着面前的城墙大叫。
就在这时,远处的胡商营地方向,突然亮起数十道耀眼的光束,那是无数巨大的玻琉璃器将阳光汇聚过来的炽热射线。
郑据和车禅儿一起抬头,绝望地看着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烟尘爆发出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冲击波。
“法信”被剧烈的爆炸震得几乎死去,此时死囚的监牢都已经被炸得倒塌,但他趴在稻草上逃脱不得。
“突昏!突昏!”他忽然听到同伴们的叫声,是他在城外的那些胡人同伴。“法信”睁开眼,看见杀进城来的“胡商”们。
他们跳下马来,将法信搀扶起身。而他们的首领正骑在马上,握着血淋淋的弯刀,他看着“法信”,叹息道:“突昏,你受苦了!”
“今日我们便要屠尽此城,为你报仇!”“胡商”们突然义愤填膺地大叫起来。
“等一等!”满身是血的“法信”突然挣扎着抬起头,大声叫道:“屠城……算得了什么!”
“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连中原朝廷都可以一起毁掉。”“法信”抬起头,吐了一口血沫,神情狰狞地狠狠说道。
一行人在“法信”的带领下,穿过已经半数被炸塌的城中建筑,摸到了原本靠近城墙的悟空住处。那座破屋果然没能经得住剧烈的烟尘爆炸,已经化为废墟,但是所有人都看到废墟上,那座原本藏在悟空肚子里的佛像,正歪歪扭扭地斜插在废墟里。
“就在这里?”胡商首领说道。
“是的,我那时翻了书信才知道,悟空那老和尚从天竺带回来一颗价值连城的佛舍利,本想带回中原。但是那郑据拦下了他,说那时中原朝廷里崇、灭佛法的两派斗争激烈,舍利子一旦送进中原,势必掀起腥风血雨。”
“那老和尚也是心善,知道此事后,便发下宏愿,终生不入玉门关,留在此地供养舍利,妄图以自己一人,换天下太平无事。”
“哦?那你的意思是……”首领看着“法信”。
“我们这就找出舍利,把它送入中原,等待天下大乱。”“法信”恶狠狠地说道。
那“胡商”首领大喜过望,连声道:“如此甚好,那舍利现在何处?”
“我当时遍寻不得,现在想来,恐怕就在这里!”法信说着,一指那尊歪倒在废墟里的佛像。
“快快劈开!”那“胡商”首领欢喜叫道,旁边立刻上前两个壮汉,各持厉斧,几下便将那木雕佛像劈得粉碎。
一颗圆润的舍利子果然从中掉了出来。
“胡商”首领大喜过望,忙弯腰拾起,对法信说道:“我这便命人将它送往中原——”
他还没说完,法信已经扑了过来,一口将他的手指连同那颗舍利一起咬下。在首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里,法信满嘴鲜血地大口咀嚼着。
“你干什么——啊!”首领疯狂地跳脚大叫,另一手拔出刀来,狠狠劈在了法信脸上。
法信怒视着首领的视线最终被鲜血覆盖,他的双眼都被这一刀劈碎,但他仍然大口咀嚼着,凶狠地叫着。
“你不要再想害任何人了!”
“啊啊啊啊!你这叛徒!我活剖了你!”“胡商”首领声音都嘶哑了,接着便是弯刀劈下的声音。
“铛”的一声,那刀被一根横伸过来的棍子招架。接着满身是血的法信被人拎上马背。
“走!”法信听出那是车禅儿的声音,他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
车禅儿骑着马,载着法信一路颠簸朝东而去,一路上喊杀声、刀剑声连绵不绝。不知过了多久,车禅儿才停下马来。
“你骑马继续朝东,去敦煌。”车禅儿翻身跳下马,对仍坐在马上的法信说道:“到那里才安全。”
“那你呢?”法信惊恐地抓住马鞍叫道。
“接下来你要自己走了。”车禅儿说道:“我……我要回去,和郑大人一起战斗。他还在城里。”
“禅儿!”法信什么也看不见,这时马匹已经自己开始跑了起来,他惊慌地俯在马背上,大叫起来。
“你不用怕,它会带你去的。”车禅儿的声音已经停在远方,她顿了顿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笑意:“你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你放心,我已经不再怪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那马长嘶一声,带着伏在马背上哭喊的法信绝尘而去。
数十年弹指一挥间,敦煌城内,垂垂老矣的盲和尚法信盘坐在城东索使君家中的佛堂内,正和主人家的孩子模仿着受戒的仪式,做着一般孩童不会做的游戏。
这孩子总是喜欢缠着脸上横着一道狰狞伤疤的法信,尽管那道伤疤横穿了他的双眼,让他双目不能视物。
所以这一次,主持受戒的是这个孩子,他按着法信抄写的《受十戒文》逐字念道:
“尽形寿不杀生是沙弥戒,能持不?”
“能。”
“尽形寿不偷盗是沙弥戒,能持不?”
“能。”
“尽形寿不妄语是沙弥戒,能持不?”
“能。”
“尽形寿不饮酒是沙弥戒,能持不?”
“能。”
“尽形寿不淫欲是沙弥戒,能持不?”
“……”
“暂时因缘,百年之后,各随六道,不相系属。”
“……能。”
“咦,这后面是什么?”那孩子念罢,又把抄写经文的纸翻过来,发现上面誊着四句小诗。
“日月长相望,宛转不离心。见君行坐处,一似火烧身。”
这孩子哪懂呢,只怔怔地看着掩面颤抖的法信。
<完>
作者:埋名
作品:《死者留言》发表于银河边缘,《下生》发表于蝌蚪五线谱
审核专家:罗琳 重庆科普作协副理事长
蝌蚪五线谱原创科幻小说,转载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