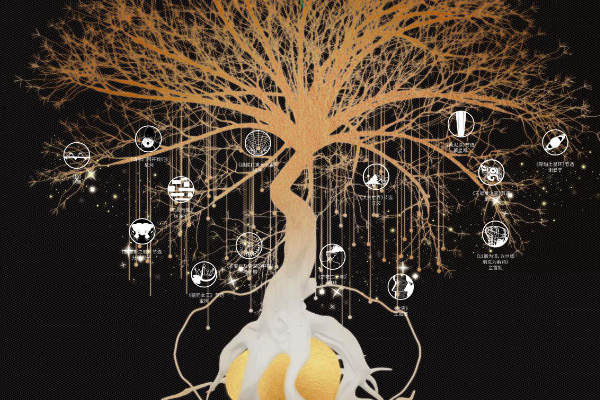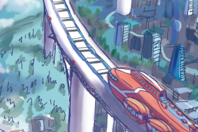红盒子
第十届光年奖校园之星一等奖
(1)清洁工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盒子,但没人知道怎么打开。
直到二十天前还不是这样。盒子上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缝隙,用精密的仪器也判断过了,没有机关、密码、特殊的结构。盒子是八个圆角、十二条圆边的近似正六面体,通体是均匀的红色。自然界能见到的水果、矿石、花朵、鸟羽、太阳、火焰,它并非任何一种,也不是255,0,0调出的电子红。在现实中找不出对应它的颜色。
我们用了激光,金刚石,外力挤压,许多许多。它的性质始终一动不动。来自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建议我们首先采样进行分析,被否决了。因为它的外表是绝对光滑的平面和曲面。
“我不记得谁把它放在这里。”研究所最有资历的老所长,最后给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在搬动办公室那张旧椅子时发现它的,那把椅子早就坏了,四条腿有三条不一样长,那时候红盒子塞在最矮的一条腿下,被毛毯般的蜘蛛网盖着。
当时,不知道谁走到旁边,脚尖轻轻碰了一下红盒子。他或者她做这个动作纯粹是出于无意识,当盒子被这一下撞击推动,贴地飞了出去。他或者她想必也是下意识去抓,就像抓一只普通的盒子或普通的老鼠,但第一次显然没抓住,而只是偏移了盒子的速度方向,第二次则给盒子以加速的力,让捕捉变得更为困难。
盒子从房间左侧滑向右侧,直朝着门的方向滑行而去。发现者目测了一下距离,又心算了地面的粗糙程度,发现它会停在离门框约半米处。因此,发现者一只手扶着已无法自己平衡的坏椅子,另一只手在椅背上弹奏无声悦耳的音乐,沉浸在等会儿下班吃什么的想象中;红盒子则不紧不慢地穿越大门,通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这是红盒子注定要被发现的幸运——这扇门正对着楼梯。在楼梯顶端跳起,斜着滚下梯级,被楼梯拐角的两面墙碰撞反弹,如光路在方形镜阵里折射;红盒子一路朝楼下狂飙而去。
楼梯通向一百二十八米长的灰色走廊,红盒子以每秒三点二六七米的速度匀速前进,七次从路人两腿之间穿过,二十九次撞在墙上改变方向。而几乎每次路过,都闯入未关好门的实验室,往潜心于培养皿、电路板或移液器的白大褂裤腿,不痛不痒地咬上一下;然后,在他们后知后觉的左右不安中溜回走廊。
在接到第三份出奇一致的“实验室异常物报告”之后,我的部长产生了警觉。他召集我们开会,简单讨论了恐怖分子入侵说、异国间谍窃取说、秘密实验失控说、外星生物打招呼说这几种可能性,并说我们没有时间再多做讨论,快去抓那可能是炸弹是无人机是外星科技或者不可告人秘密的东西。以我为首的安全组员集体带上最昂贵的设备,自从我们调到这个部门,就再也没遇到过和实验失败同等刺激的事,我们都期待着一场惊天动地,能为基地报纸提供三十天头版新闻的大抓捕。
我们赶到时它正在电梯里单线往返,“咚”“咚”的清脆之音显示出它永不会疲劳,可就连被它反复碰撞的金属梯箱也迟早会疲劳;金属面倒映的三个影子和它一起运动,像轨道上和轨道下同时行驶着两列火车,而轨道侧面还挂着两节车头。
想象中的大抓捕很快变成狼狈的健身房。抱着干扰仪的Y不敢被碰到(“万一爆炸!”),又不能磕坏仪器,只好将十多斤的铁家伙架在肩上跳脚;双手持隔离器的H试图靠深蹲接近它,再双手托着隔离器向下捕捞,远远望去如倾倒痰盂状;C拿推车运来了应对系外生物的全套指南,这套指南存放在一千米以外两层楼以上的资料库,C的肚腩仿佛变薄了几个夏天,其他人则给他眼神示意他“别兴奋了不是外星人”。
我们很快放弃了直接尝试,退出来重新商讨。C首先表示,这玩意儿飞得这么快,多半不是地球人造的,H坚持说让他再试一次就能抓住,Y轻抚干扰仪洁净的表面,别人伸手碰他就龇牙。讨论进展艰难。其实要抓住这东西并不难,但到底用哪种装置,抓住之后要做什么预防措施,又要怎样在狭窄的电梯间完成这一切,我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之几同时调动却一筹莫展,时间很快过去了。整点钟声敲响,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谁都没有注意她,或许她的日常身影已融入实验楼走廊本身,以至于她的出现不让任何人感到不自然。她(比我们中大多数人矮小半个身子)从走神的Y身边路过,钻入H和C争执时胳膊抬起的门廊,两手拿着她的东西进了电梯。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之前,她已将那东西横过来放在地上,红盒子像只煮熟的螃蟹横着走进蟹笼,“嗵”一声扎进垃圾桶,她立刻将桶翻转过来,桶口朝上,轻拍边缘问:这块塑料你们还要不要,不要我卖废品咯?
这件事的结果是,清洁工因为违反规定被调离了原职位(“谁知道她那么干会不会爆炸”,组长一边在垃圾桶里掐灭烟灰一边说道),但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和极高的待遇,足够她养老到把这个事件带进坟墓为止。我们全组则被提升为“红色不明立方物体问题研究第一小组”,并因在突发事件中的窝囊表现被狠狠地训话一次。
红盒子问题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科技。
红盒子现在装在一只特制容器里,容器是透明恒温的,其中盛满了浅蓝色液体,以便缓冲红盒子的运动,减少器壁的损耗。红盒子从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恢复静止状态,关于是否要带它进入太空的提案已经在讨论。
在试过一切可能切动它或造成形变,却哪怕是刮一撮粉末都做不到的物理方法后,我们尝试用化学方法来打开它。二十天足够我们最精锐的团队研发一种新溶剂,尽管这只是几种旧溶剂的重新混合。
最奇怪的是,我们收集了红盒子途经路线上一切的样本,却没有找到和建筑环境不同的材料,即使是最有可能的垃圾桶和旧椅子也失败了。红盒子摸起来冰冷坚硬,没有反光的金属质地,几乎没有导电性,耐高温高压,再加上其他的研究结果,我们推测它是种高分子合成材料。如果是竞争国研发的间谍仪器,就很有可能是使用了某种新材料,这大概是它强度如此高的原因。我们担心这只小盒子里藏着帝国的窃听器,每次接近它时,哪怕是在谈论关于它的事,我们也会放低声音,甚至控制脚步。到后来,我们一见到它,脑子里就长出敌国情报机构的种种传奇故事,以至于见到它的那一刻连呼吸声都停了下来。组长在会议争论不休,吵吵嚷嚷时总把它掏出来(许多时候是复制品),效果立竿见影。
为了测试溶剂的效果,我们用惰性网将它捞出来。空了的容器像只蓝色胶囊。三,二,一。倒数三声,我们将红盒子送进腐蚀效果极强的液体,并立刻捞出来。假如动作太慢就会破坏盒内的物品。只是红盒子似乎比想象得更加慢热,我们不得不再次放回冒着泡泡的腐蚀液汤汁里,等它慢慢炖成又软又烂的方块。但直到这一天的结束都毫无进展,红盒子的圆角还是同样的直径,而当我们洗干净它要为它擦去附着的液体时,因为一个草率的放置动作,它从桌上直接弹射出去,猛击在腐蚀液的废液中,飞起的液滴把实验室的墙打成了胃溃疡。这更是表明它的光滑表面依旧绝对光滑。
“打开它就那么难吗?——难道打一个洞也不行?”
为了替红盒子问题选拔人才,政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培养了比原定多百分之十七的材料学家,这些材料学家有许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为寻找一种可以切动红盒子的材料而反复实验,在这过程中我们成功找到了金刚石的工业替代品。我们甚至将目光投向生物科学的领域,号召下一个世代的青年普遍投入到这一学科中,因为纯粹材料上的进展实在令人失望,特异细菌分解的方案显然更具可行性。很快我们培养出能以培养皿玻璃为能源的细菌,足以分解红盒子的细菌则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我们的组长将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直到他死的那天,红盒子问题仍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因此而推动的科学研究数以千万计,其中有许多技术已经民用,还有一些永远不会民用。
(2)副所长的邂逅
那是我退休后的第一周。尽管我已退休,将副所长的责任卸下,我仍然关心着红盒子秘密的破解进度。盖着各种邮戳的信件寄来我的私人邮箱,怪异的发明在快递站被拦下,花一生构建一套体系的民间理论者试图隔着院墙和我讨论。收到那东西我并不惊讶,过去的几十年人们给我和我的同事寄各种东西。我唯一惊讶的是,它是怎么直接进入了我的浴缸。
那东西外壳泛着彩虹肥皂泡色彩,既像邮筒,又像电话亭。一位红眼蓝肤,头顶伸出菌帽状触手的类人生物扶着邮筒电话亭,二郎腿从浴缸翘出来。
“你好。”那皮肤应该不是真的,我心想。
“你好。”
红眼类人并没有张嘴,声音却从接近它肚脐的位置传来。我猜他或她是个腹语师。
“请问你有什么事?”怪人,乃至疯子,我也遇到过;但只要能交流,就有可能达成一致。更何况只是喜欢cosplay外星人的怪人。
“人类。我来自未来,未来的另一个星球。”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它的声音听起来中性化而平坦,就像把全人类的音色叠加在一起,再取最大公约数。我意识到一点问题,因为它的触角出现了明显的上皮细胞脱落。观察这个就意味着相信,那数十条状如蓝色蘑菇的东西,是它身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可以让一切变得可怕。
“啊,未来的外星人……那么,你、你为何而来?”
“首先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吧。你现在看到的外貌并非我的真正外貌,而是我模仿你内心最向往的女性形象而成,请不要浪费时间,来询问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年代,‘红盒子’已经成为科学精神的代名词,不管历史怎么发展,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上周我们新建设的月面虫洞就是以它命名的。”
“所以,你们需要我这个古代人来做点……呃,文化认同上的工作?”
这和我的想象有些不同,索性不是坏事。
“不。”蓝皮肤,红眼睛,穿着白紧身衣的女子摇摇头,“红盒子关系到这个世界的真理。而我们新研发的仪器可以解决这个终极问题。”
那么红盒子问题本身还是得不到解决咯?我正这么想着,不禁想起他们的时代可能有读出脑内想法的技术,立马掐灭了这种略带嘲讽的观点。
研究员的表情没有异状,不知是没发现还是习惯了。她指着那东西:“这是一个处理器。”
“什么?”我没有想到,科技发展了,CPU的体积却退步得如此明显。这么看来,未来人是重复发明了CPU吗?但我想不出他们重新需要晶体管计算机的理由。
“处理器。”她咬字咬得格外方正,似乎是怕我没有听清。
“我知道,但是……”
“你不知道,因为这东西还没录入数据库。”她微微一笑,而后笑容像折叠剪刀收了回去,“刚刚那是个笑话,希望你喜欢。”
我举起双手表示投降,等着她解说“处理器”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新发明。事实上,我们也不太清楚它的原理……”
“这是怎么回事?”
“说是发明,我们只不过是想出一个点子,再把可用的零件和套件组合在一起,达到预期的功能。我们可以说出的原理非常有限,就像你可以看见一个人活动手脚,如果你懂得一些生理知识,会知道他在用哪些骨骼哪些肌肉。但是再底层的逻辑,我们就说不出了,就像一块肌肉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功能,或是骨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硬度。”
我看着她显而易见的非人类躯体,对她能够想出生理科学的例子感到无比震撼和感动。
“也就是说,这东西算是个黑箱?”
“部分如此。”
“那么它的功能到底是?”
“很简单,我来示范。”
她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物件,我看见那是打火机——她立刻解释人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古董了。她拉开处理器的门,我只看到里面有一个漂浮在半空的台子,她将打火机放在台上,自己站在一旁,说道:“点火。”
我确信自己没有眨眼,没有走神。我确信自己的人类眼睛以人类的刷新率洞察着一切。但我更加确信,在那一个瞬间,处理器内的空间被置换了,我看见打火机由关闭变为打开,不是看见改变的过程,而是直接抵达变化后的结果,一簇火苗冒了出来。
当她结束这仿佛变戏法的环节走出来时,我还在迷惑和怀疑中。
但当我想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由得惊呼出声。
“这特么的根本就不科学啊!你到底对这个打火机干了什么?”
她将打火机取出,我注意到,打火机的一角离开处理器范围的一瞬间,打火机恢复了关闭状态。
“我刚刚说了,这东西是个黑箱。”
“严格来说,那应该是我说的。”
“这不重要。总之,我再次说明,我不能解释它是怎么运作的,我只能告诉你,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这我知道。所以这该不会是……”
“套用一句俗话,‘心想事成’。”她指了指自己的,应当是太阳穴的位置,“足够清晰的念头可以驱动现实世界的变化,尽管只存在于处理器的空间区域之中。我个人认为,可以将它看成一种模拟,对真实世界可能性的模拟。……哦,什么?‘心想事成不是俗话是成语’……收到了。”
她果然会读心。我晃了晃脑袋甩掉这个念头。当我再度睁开眼,更加吊诡的事发生了。外星人或曰未来人,她消失得无踪无影,只有处理器仍卡在浴缸中,连刚刚还在的打火机也消失了。
我失眠了一晚上,身上像盖了冰块,又像发了高烧。我根本不信。平静的退休生活里闯进来的东西,给我太大冲击。
从科学上看,时间穿越和外星人都是可能性的产物。但当你被事实冲击得七零八落,一切你学习、遵循、思考的科学法则都会变成废纸。
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太久。七天之后,我紧张地走进浴室,第一次试着复现外星人的操作。只不过我不抽烟,用的是火柴。当我酝酿了数分钟的嘴唇开合,说出“点火”时,平台上的火柴变化了。它们站立起来,围成一圈,火柴头烧起了火焰。我不甘心地尝试了更多次,又把尝试的内容改为对盒子使用“打开”,对牛奶使用“沸腾”,对睡衣使用“折叠”,可是没有一次失败。
我翻来覆去,又失眠了更严重的一晚。为了确保我晚年睡眠的幸福,三天之后,我决定只能把这东西上交给组织。
(3)言语的法术
“是的,所长,已经有几百位研究员想报名参加验证‘处理器’有效性的实验了。我们会尽量筛选,那些想把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放在平台上,说出‘变大’的研究员,我们会阻止他们的。是的,我们和他们说过了,这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变化只能保持在处理器范围以内。……但我们是否应该满足副所长‘长出毛发’的请求?”
“我看看申请表。对实验报告说‘请自己完成’——张工,别想偷懒。对十年前的自己说‘别加入时间穿越研究小组’?这意味着你们小组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嘛!对办公桌上忘了太久而坏掉的曲奇说‘复原’?嘎吱,唔嗯,没什么创意,嘎吱嘎吱,唔嗯,但值得一试——唔嗯?这块曲奇味道怎么……”
“蟑螂——种族灭绝
(未通过。批语:这恐怕看不出结果,放心吧,处理器里不会突然跳出蟑螂)
芒果——去核
(通过。记得分我一半)
冰淇淋蛋糕——变成火麒麟蛋糕
(通过。)
(补充:这位语言学家关上了门。拒绝让我们分享他看到的结果;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他的下一篇论文)
《红楼梦》80回抄本——由原作者写完
(未通过。原因不明)”
“第一千零一位志愿者,他走进去,像其他所有志愿者一样,把红盒子放上去,对它说‘打开’。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是的。是的。我们会暂停测试。好的。好的,我这就通知理论部门继续研究关于……”
(4)得其环外
新所长看着桌上的辞职信,从字迹可以认出来,这是三个月前接下那项任务的研究员。他从前的工作是观察其他部门培养出的培养皿,他申请调动是因为感到厌倦。他的新工作是每天站在处理器里,对红盒子说一千次“打开”。
副所长的遭遇的确给红盒子计划带来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这进展全是在红盒子以外的学科。有时新所长也会想想,哪怕红盒子永远不打开,也未必是坏事。
现在想起,最早声称红盒子是“盒子”的说法,已经不可追溯了。所有人将它视作最先的公理,基于此去思考关于红盒子的一切。但是,假如是最早那人做出了错的判断,红盒子根本不是盒子呢?既然还没有打开它,那就什么都不能说。
所长端起茶杯,去向新来的研究员介绍红盒子的情况。这是研究所的传统。
新研究员刚从学校毕业,看起来还有些稚嫩。很可惜,她马上就要变老了。所长不由得在内心里斥责起所里的工作强度。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员。关于‘红盒子’……”
“我有问题。”长相温柔甜美的女研究员,声音却显得格外神经质。
“请讲。”所长有些不悦,但所长很有礼貌。
“首先,为什么说它是盒子?”
“嗯,这,这是因为,我们最早对其内部密度是否均匀做出了判断。这判断很容易的,对吗,就是那个,那个,最常用的那种方法。那么关于——”
“那么我还有问题。”
“……请讲。”
“为什么说‘我们尝试过许多次,始终打不开盒子’?”
“因为——因为这是事实!”所长开始感到莫名其妙了。
“但我们是怎么确定的?我们怎么确定盒子此时此刻是‘关上’的?”
“因为用肉眼……”
所长愣住了。新研究员接着说:
“之前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处理器内,绝大部分的物品都可以顺利完成变化。之前也尝试过各种箱子,只要说‘开’‘打开’‘开启’等意义相同的词汇就能开启。我研究过那些不能成功的案例,往往是因为说话者脑子里的概念本身就不明确——什么是‘火麒麟蛋糕’?长得像火麒麟的蛋糕?品牌名是火麒麟的蛋糕?火麒麟味的蛋糕?而谁又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写完’是写到哪一部分预先可以得知的情节为止?也就是说,限制了可能性被处理器展现的原因,是我们的认知无法超越已经缺失的现实。对盒子来说,在‘开与不开’这个维度上只有两种可能。但什么是盒子?立方体就是盒子吗?表面规则就是盒子吗?假如这个盒子实际上已经打开,不论呼唤多少次,它也不会再度‘打开’。假如它实际是关上,当我们说出‘打开’时,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跳到‘关上’的反面,唯一可能的阻碍是,我们过去做出了太多暴力破拆它的尝试,这种根深蒂固的……”
“很好,很好。”所长连忙打断道,他庆幸自己一句都没仔细听,“你说的很好,我们现在就去试。”
虽然所长仍在怀疑红盒子到底是不是盒子,但他不能在下属面前显示。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红盒子的确是个盒子,他完全没意识到,这和他几分钟前的主张完全相反。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打开,打开,打开……所长?请问我的辞职……”
“最后一次!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我马上就让你去其他岗位。”
眼神疲倦又迷离的研究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继续转头面向红盒子,说“打开打开”。
所长叹了口气,说道:“关上。”
研究员停下重复,转过身来。处理器常年开着门,但门的界限依然存在。研究员在里,所长在外。所长又说了一遍:“关上。试试。”
研究员发呆的时间超过了所长发呆的时间。因此,所长还来得及看到他关门的那一幕。几秒后,在闭合的处理器里,研究员大喊道:
“好了!”
所长激动地打开门,正想问“什么”。这时他看见平台上的红盒子,距离太远,看不清是否有变化。
被吓到的研究员向后缩着身子,发出一声惊呼:“出去!”
这时候,所长依旧在门外,研究员依旧在门内。所长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看到红盒子的人。红盒子听懂了研究员的最后一句话语,它再也不在处理器之中了。它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红盒子的突然消失造成了许多混乱。一些人被免职,另一些人终于被免职了。基于红盒子建立起的学说在短时间内受到质疑,在长时间内关注度提升。曾经以解决红盒子问题为志向的年轻人纷纷转向,世间又少了一些意志坚定的人。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的不幸,红盒子的支持者仍然相信:在宇宙某个角落,深邃的黑暗里,红盒子仍在为某把无法自立的椅子持续提供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