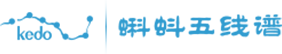短篇小说二等奖-《致橡树》
变成一棵树是什么样的体验?
我好端端上着班,唱着歌刷着业绩,突然就被抓去做了树。
那是个阴雨天,我的心情跟窗外绵绵的秋雨一样糟糕。
一大早,行政部的小妹就将上个月的基金销售额贴了出来,我做的很出色,业绩排在榜首,但很快我就后悔那样勤奋。
晨会上,BOSS红光满面,嘴角十分夸张地往上扬起,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线。显然,他对我的表现相当满意。
“伍德,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下个月可要保持啊,继续努力。”BOSS带头鼓掌,台下响起一些稀稀拉拉的附和声。
我的好心情只持续了五分钟。
因为,这个死胖子接下来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指标:下个月上调16%的预期业绩。达不到?奖金减半。
16%!短短的一串数字,我的喉咙却咕咚一下,汗珠浸湿了发梢。
这时,办公室外忽然骚动不已,紧接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闯进了会议室。我抬头看了一眼,继续整理自己的文档。同事们习以为常,纷纷碰起了头:“又是哪位拿不到执业的实习生,要被抓去做树了吧?”
所谓做树,事实上是一种普通的工作,更官方的说法,叫作拟植。
这种工作,可有些年头了。
七十年前,一种特殊的宇宙射线造访地球,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植物杀戮殆尽,那一天被称为“灭绝日”。科学家们给射线取了个名字,叫做z射线。至今,科学界仍没有弄明白z射线的伤害机制,只知道它会破坏植物细胞的内部结构,使之迅速脱水,直至死亡。植物界与动物界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唇亡齿寒,社会受到的影响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全球缺氧,大气成分剧烈变化,水土流失,支离破碎的生态链,以及漫天遍野的黄沙,都是z射线造访地球后带来的礼物。
对如今的地球来说,一棵健康茁壮的大树,比一个成年人类的作用更大,也更珍贵。我们从小就被种植下各类苗种,这些苗种像病毒一样潜伏在脊髓的神经元中,以期未来。家里条件不错的,接种的都是观赏苗,牡丹,玫瑰,郁金香,我们叫它爱豆型苗种,属于不事生产的艺术界人士。普通苗种就悲惨多了,比如最常见的橡树种,注入营养液塑形拟植之后,橡树人对水土流失极有帮助,放氧量又大,生长中的副产品--橡木,也是上等的建筑材料,所以多数都被移植到林场,作为市政工程的一部分。仙人掌种耐旱,则是大西北的人们所喜爱的苗种。
成年后,如果拿不到大学毕业证,或是各行业的执业许可,就只能去做一棵树,十年后才有机会重返社会。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法案不太人道。
不过,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生物。我既然已经投身社会,摆脱了法案的束缚,当然不会真心地关注一棵树的权益。
等到纷扰的会场安静下来,我这才发现,军官站到了我的身后。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照片,稍一比对,便作势要拉我起来,“伍德,你被市政厅指派为一棵树,请尽快交接社会事务。”
我瞪大了眼睛,连忙开口,“长官,我有大学文凭,投行执业资格,按法律来说,我应当拥有拟植的豁免权。
那军官的目光像两把刀子,看起来是个狠角色,他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提高了声调,“昨天刚刚生效的紧急法案,所有橡树种的公民都要进行拟植。”
士兵们列起队,像转移囚犯一样,将我们这些橡树种的倒霉蛋带出去。
我回头看去,那些幸免于难的同事们神色各异,但都十分惊恐。
我想,这大概是一场误会。
荒谬!这居然不是一场误会,我的名字赫然登记在名单的第一位。
他们将我带到市郊的林场,关进了林场外围的一幢大楼里。我找到看守的头目,大声争辩,想要博得他们的同情。
我他妈可是个金融天才,大学时专业课年年考第一,进了投行也是业绩明星。因为我是橡树种出身,就让我来当一棵树?这绝对是暴殄天物。
林场的法律顾问抱着手听完了我的陈述,摇摇头,对我进行了一番普法教育,“所谓法律的权威,就在于没有人可以违抗,众生平等。”
“金融业?投行?那就更该如此。”看守们嘿嘿地笑,目光锐利,像一群见到猎物的野狼似的。
我脊背发凉,往后退了好几步。
每个人分到一支注射针,一副吊瓶,以及一大罐绿色的液体。有听话的,已经排着队去接受注射,只有我张牙舞爪,想要撬开那扇钢制的自动门。结果,我受到了一份特殊的礼遇:两个身强体壮的士兵将我一路抬到了注射间,医生连正眼都没瞧过我,就将针管扎进我的静脉。
我手臂一凉,真切体会到了法条的冰冷。
注射营养液的时候,负责我们这一组的园丁就站在我的面前,步履沉静,腰板挺得笔直,冷冷地看着我。十年的拟植期里,他将是我的直接上司,或者说,对我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管理人员。
我仰起头,只能看到他瘦瘦的下巴,上面仍有少许未剃净的胡渣:一个粗线条的壮年汉子,不管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不太好惹。
营养液输入我的体内时,我身上冒出一阵冰凉的触感。我看过关于拟植的书,高中时学校还开设过几堂专门的讲解课:出现这种冰冷的触感,代表着我的感觉器官正在发生变化,从感知物体的细节开始转向感知风量与阳光,我正在从人类变成一棵树。
一个树人。
好几次,我都想要拔掉针管,但只要对上园丁的眼睛,手脚立即松软下去。
我毫不怀疑,他会当场甩给我一个耳刮子。
吊瓶里的液体是碧绿色的,流动时有着荧荧的微光,看起来十分妖异。这些液体正通过长长的针管流进我的静脉,手臂上的血管随之缓缓贲起,有节奏地上下起伏,像是主动吮吸似的,饥渴极了。
变成一棵树,执行一棵树的使命。这听起来很正常,但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做一棵树,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这不好么?”
注射阶段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不知道为什么,我全身发虚,连站起来都有些勉强。园丁搭了把手,将我扶到休息间的沙发上,似乎想从思想上征服我。
“你懂个鬼,我是个投资好手,我天生就属于投行,十年拟植期?一动不动?我宁愿死掉。”我的声调陡然升高,吓了他一跳。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在考虑接下来的措辞。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都是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出力,哪里分什么贵贱。”园丁慢条斯理地说。
“如果让我回到从前,我肯定愿意接种橡树苗。我热爱林场,它是城市之肺,所有生命的保护者。”他忽然将语速放慢,似乎想起了什么,言语里有说不尽的惆怅。
我愣了一会儿,摇摇头,为自己的冲动羞愧不已。第一次与园丁见面,就朝他这样发脾气,也确实过火了点。
“十年而已,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你尽管做你的基金经理去,如今,也算是为国家出一份力。”他摸了摸下巴,表情缓和了许多。
我瞪他一眼,忽然想到什么,便问他,“今年的大气环境坏成这样子了?要把我们这些社会人拉到林场。”
我看过植物局前几年的报表,客观上来说,情况不算太糟。
他叹了口气,“我也不清楚,但是听市政的同事说,灭绝日的影响还在继续,说不定会变得更严重。”
“下一波大范围的z射线就要来了。”
听到这个词,我一愣,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什么,刚刚嘴还很快的园丁也沉默下去,一种莫名的感伤笼罩住了我们。
从前,森林是人类的保护者,z射线肆虐之后,人类就要靠自己了。
“这回的绿液有过改进,听说...你可以用根系走来走去呢。”园丁打破了沉闷。
“那不还是树?”我的心情又低落下去。“早知道,就该搞土壤工程,再怎么样吧,也比做一棵树要人道一些。”
五十年前,邻国曾流行过一种应对措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遇到大气缺氧,便用化学方法制备放出氧气,水土流失,则通过变换土壤成分改善。但很快,这种办法就宣告失败,因为大气的成分总是达不到最完美的比例,土壤在人为干预下失去肥力,饥荒也时有发生,这让所有人意识到一件事:自然界的平衡能力远超人类。
“从价值上来说,一个树人的投入与产出可经济多了。我们有四百亿人口,这是一种廉价的资源。”园丁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我立即缩起头,感觉脖颈里阴丝丝的。
二.
我盯着镜子里的那截木头,心里凉了一半。
从人到树,转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昨天我还在清理鬓角的硬茬,到了今天,下巴上已经长满了嫩绿的细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得茁壮。
我拿起手机,对着最后的影像拍了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上,打算留作纪念。
没两分钟,电话就响了起来,我一翻屏幕,是母亲打来的电话。
自从大学毕业,我和她已多年未见。母亲是个保护欲很强的人,一直将我当成温室里的花朵。我上大学时,女友学的是拟植学,母亲听闻后,态度强硬地表示反对,那时我年轻气盛,自然不会乖乖听话,所以我与她的关系处的一直不好。听说,父亲是死在一家林场里的,母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乃至迁怒于所有拟植相关的东西。我将女友的专业告诉母亲时,无异于在她的耳边杀出个晴天霹雳。
“你去做了树人?”母亲的嘴唇不停颤动,额头上满是汗珠,看起来很紧张。
我向她解释那部刚刚生效的新法案,让她不要担心。
她的嘴角向下,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母亲忧心忡忡,“你现在在哪儿,我立即搭飞机过去。”
这场交流以我主动挂断电话而结束。母亲虽然远在北方,她的一些举动却仍会让我心烦意乱。
不过,做树人的日子,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
每周工作六天,周日则被林场留了出来,用作树人们检查休整。这一点,总算还有些良心。我的工作内容也绝对不算复杂:站立。
甭管下雨下雪,哪怕天上下刀子,我们也得老老实实地站着。
我们这一组有两百多人,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同期林。种植区在林场的一个偏僻角落,周围很荒芜,到处是猩黄的沙土。坑洞早就挖好,树人们只需排着队,一个个跳进去而已。园丁负责帮忙铲土,掩上那些密集而脆弱的根系,有时还得帮忙清除虫害。
老实说,我很不习惯用根系走路,那玩意的体验太糟糕了,总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章鱼,在地上滑来溜去。幸好,我们走路的机会不多。在工作日,园丁往我们身上浇营养液,这让我们昏昏欲睡,迷迷糊糊地熬过144个小时。
我想,若是从天空向下俯视,林场的规模一定很壮观吧。十多万个树人,按照既定的格子区,整齐均匀地分布在一整片原野上,在微风的轻拂下,头顶嫩绿的叶子沙沙作响。这些经过精密改造的树人们没有植物的结构,轻易避过z射线的伤害,却又拥有强大的光合能力,承担了绝大部分换氧工作,维持大气比例的平衡。
周日,则是我们的自由时间。愿意的话,你可以用根系慢悠悠地爬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会儿手机,发几条微博,与旧友们分享这份沉闷的工作。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待在林场,连根系都不用挪动:那儿可有十多万人,光是找不同的人聊天,都可以聊上十年。
我最常去的地方却是医务室。
我已经认命,想要安安稳稳地度过这十年拟植期,将来领了补助金,好好做我的基金经理去。但我这副崭新的身躯,却一直在跟我唱反调。
全身皮肤逐渐变硬,甲化,颜色越来越接近橡树,头顶与肩膀则长出枝桠,枝桠上又冒出一些嫩叶,到目前为止,这都很合理,也符合园丁告诉我的生长进程。
不过,我的状况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最先发现异常的人,是个小胖子。他的种植区与我仅一步之遥。小胖子曾经是个美食博主,对吃充满了热情,被抓到这儿来做一棵树,无异于杀死了他的梦想,但他有着随遇而安的天性,很快喜欢上了这项工作,并且树围的增长速度比我们快得多,这成了他自豪的资本。
“伍德,你该让园丁大叔给你多浇点水,瞧把你瘦的。”他总是笑嘻嘻地挤兑我。
园丁倒是很高兴,上个月底,他大张旗鼓地宣布,树人比赛的结果统计完毕,小胖子是林场的换氧冠军,场部甚至颁给他一个先进工作者的标牌,用红绸布卷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
那天是个寻常日子,我注意到小胖子的眼神一直在我的身上转悠,可我的根系困在沙土下,又不能转身离去,只好瞪他一眼,“看什么看,没见过树吗?”
小胖子看起来很严肃,他在我身上打量了好几个来回,斟酌地说,“伍德,我觉得你的身体似乎有点问题。”
按照小胖子的说法,作为本林场树围最大的人物,他一直很关注其他竞争者的状态。然而,我的发育速度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刚到林场时,我的体型只有他的一半,可是才种下两个月,我的树围就已经堪堪追平了他,似乎还有着继续疯长的态势。
我的心里一惊,怪不得自己这么难受。树人的感知比人类迟钝,这一点我是明白的,然而我的感知能力却反了过来,比为人时还要敏锐地多。天空飘过的云朵,拂过我脸颊的风,根系上正在吸取汁液的蚂蚁,乃至于身下土壤的呼吸与律动,都在我的感知范围里。
感知力起码被放大了十倍,这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就像你躺在床上,想要安安静静地睡个饱觉,却清晰地感知到整个卧室的温度,湿度,乃至床底的某一粒灰尘,翻身时床架的咯吱震动,窗外的细微风声,这些我不关心的东西,一股脑儿灌进我的脑海。
这种现象肯定不正常,我只是树人,并不是一棵真正的树。
园丁的眼神意味深长,我想,他一定早就发现了我的异常。
到了周日,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挪到医务室,走的太急,根系上起了很多水泡,疼的要命,可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嚷嚷着找医生。
穿着绿大褂的医生绕着我摸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犹犹豫豫地开口,“也许是中年发福。”
我伸出手,一把攥住了他的肩膀,手掌上的枝叶一片片竖起来,向他表明我内心的恼怒,“医生,你可得仔细看看,我这腰围明显不正常。将来拟植期满,我会恢复成什么样?一个大胖子?”
医生被我的表情吓到了,哆哆嗦嗦地又摸了一圈,还拍了张片子,对着荧光灯左瞧右瞧,仍说不出半点端倪。
“再观察,再观察看看。”医生看起来拿不定注意。
我这才道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如果拟植异常的话,是不是该把营养液抽回去?也许,我就不适合当树人呢,腰围跟个水缸子似的,要是将来找女朋友什么的,影响也太恶劣了。”
医生连忙摇头,“管控拟植进程,那是园丁的职责,我只能做出判断,没办法帮你。不过...你的成长数据确实有点怪,关于中断拟植这一方面,倒也有一定的指征。”
我的眼睛立即亮起来,朝医生点点头,接着看向园丁。从我进了医务室起,他就跟了过来,一直站在我的后面,眼睛半眯着,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从他的表情看,医生的提议大概是一句废话,“男人嘛,壮一点怕什么。”
我焉了下去。
医生摇摇头,安慰我说,这种膨大现象虽然不常见,但看起来对我的身体很有好处。我的血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异常活跃,比我刚来时的体检数据好得多。
我默默地回过头,心里不知问候了园丁多少遍。
我不想要那些虚无缥缈的健康,我只想做一个普通身材的普通人。
母亲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种植区站岗。
园丁大叔巴巴地跑过来,一脸惊奇,说我有一个访客。
的确,这一年来,拜访我的人一只手数的过来。
在会客区见到母亲时,任凭我努力克制,心跳还是止不住地剧烈跳动。
我已经长到快三米高,母亲站在我身旁更显娇小。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有些心虚。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走过来抱住我,两只手臂箍地紧紧的,似乎我下一秒就要消失似的。
多年积累的小冲突,怨言,那些复杂的反叛情感,顷刻间,统统消弭不见。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关于你的父亲,关于你。”母亲低声说。
我联想到自己这副疯狂膨胀的身体,点点头,“关于我的身体?”
母亲很惊讶,“你已经知道了?”
“猜得到,你告诉过我,他是林场的研究员,一个特别专注的疯狂的研究员,”从母亲的表情看,我的内心如坠冰窖,看来我一直以来的猜测是准确的,“我记得,小时候他带我去过林场,还让我在实验室待了很多天。”
母亲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眼睛里的东西那样复杂,“原谅他吧。”
“我是个实验品。”我长长叹了口气,心里忽然空落落的。
我的饭量越来越大了。
说是饭,其实是每天例行补充的营养液和水分。按照拟植条例,林场为树人提供4ml/kg的量,那玩意儿听说不便宜,所以限量供应,在水分上倒是没有限制。
可我还是觉得饿。
头三个月,我的每日补剂量是400ml,水的用度大概在1l左右。到了入场满周年的时候,我的补剂变成了1800ml,每天还要用掉6l的水。
“啧啧,这下,你真要变成水桶了。”小胖子往我身上打量来打量去,眼睛直愣愣的。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得到了莫名其妙的改变。不管是视力,还是感知能力,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我就有些近视,虽然还未严重到“五米外人畜不分”的地步,但看远处还是非常吃力的。如今,我的视野竟然能从身下的土地,一直拉到两公里外的宿舍去,甚至连黑夜也限制不了我。从早到晚,我看着一批又一批新来的树人们加入林场,又看到拟植期满的兄弟们被家人接走,他们在林场外哭泣,拥抱,接吻,离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我都看的清清楚楚。
至于感知力,你想象过根系也拥有了细致入微的触觉吗。原先我一直把那些虬结成团的玩意当成一种假肢,走起路来相当不方便,不仅慢,而且有些硌人。到了现在,我居然可以用根系跑步,甚至比园丁养的那条狗跑的还快。
连园丁都被我唬得一楞一楞的。他目瞪口呆的样子,可真像那条狗。
我的身高,我的体型,已经让林场的所有人看出不对劲了。在这一年里,我轻松轻松就突破了林场的最高记录,长到了四米二,头顶的伞盖也大出许多倍,甚至将小胖子的头顶遮住了一半,这让我颇有些戏谑的窃喜。体型倒是还好,粗了一倍而已。
最可怕的是根系的生长。
当我站起来时,还看不出内里的奥秘,那些须根都会自动虬结成束,从外表上没有什么异常。但只要我跳进坑洞,像舒展我的腿一样,放开根系的束缚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自己的根系究竟延伸到了哪里,但土壤的广度给我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我虽然看不到小胖子的根系在哪,心里却能隐隐地感觉出来。
这应该是根系的功劳,那些长长的须根很可能笼罩住了四周五六个树人。
我看过许多关于拟植的资料。书上说,拟植期满后,树人的身高和体型就会固定下去,一辈子也不会改变。
习惯这样的外形后,我忽然对结婚失去了兴趣。四米二的身高,该找个什么样的妻子呢?
园丁大叔带着林场的大佬们过来看我,一个个交头接耳,却拿不定主意。
“我就说吧,这不对。”我嘲笑地看向园丁。
他低下头,向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抱歉,是我的过错。”
碍于身高,我看向园丁时,只能看到他的头顶。短短几年里,他头顶中央的头发居然谢掉一半。我忽然觉得这家伙也没那么讨厌。说到底,不过是尽忠职守而已。
“林场已经上报给市政厅,明天就会有专家过来。”园丁仰起头与我对视,看起来有点费力。
“不会把我抓到实验室解剖了吧?”我心里默默地想。
不过,也没多大关系了。以我现在的体型,不可能再融入社会。
林场将是我的归宿。
市政厅的专家还没来,一帮来自北京的科学家却抢先一步。
据园丁说,林场本就是一所大学的拟植学试验基地,科学家也算来得巧。
不过,让一帮大男人摸来摸去的滋味儿实在太难受了。我存心摆动树冠,让叶子到处飘洒,浇了那帮人满满一头,那帮人居然还很高兴,低声嘀咕,“这么大的树围,仍然有活动能力,确实很惊人。”|
忙活了一夜,他们取走了我身上的一块皮肤,以及几块枝桠,又往我的根系里抽出一大管汁液,这才启程回去。临走前,几个头目又嘱咐园丁,最好将我隔离起来。
这一点,我早就想对园丁说。我的根系已经蔓延到了数十米外,将邻居的水源吸了个干净,又挡住了小胖子的阳光,双管齐下,那家伙已经瘦得不成样子,活脱脱一个皮包骨,连枝叶都不再从皮肤上冒出来。
园丁大叔照办了。
与小胖子挥别后,我被移植到林场中央最重要的试验地里。那个地方原本用作实验室,如今匆匆改建,在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口,容我将自己的头顶套进去。
待遇倒是蛮高,一个教授负责我的日常护理,连浇水的工作都由他的助理,一个博士生来完成
园丁大叔将资料交接给林场的技术人员后,背着手,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一会儿捏捏我的皮肤,一会儿又摘下一片叶子放进口袋里,末了忽然开口,“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
我的鼻子不争气地泛起酸。
一周后,结果出来了。
他们说,我的身体结构与所有树人都不一样。
拟植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自z射线造访地球后,科学家们就开始进行树人培育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十年树人”法案的滥觞之始。每一个树人,都是精巧的制氧单位,奇妙的拟植生物。
但树人始终是树人,是拥有树形外观的人类,本质上仍是一种高等动物。
然而,我的情况非常特殊。
我身上的细胞居然长出了细胞壁。
细胞壁是区分动植物之间的天然沟壑,甭管是不会动的动物还是会动的植物,细胞壁是区分他们的终极手段。我轻易越过了这道鸿沟,将自己活成了树人,真正的树人。
既是树,又是人。
“那我到底是树,还是人?”我问那个笨手笨脚的教授助理。
那助理不仅手笨,连嘴巴也有点瓜,她的额头皱成抹布似的,支支吾吾地说,“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已经是一棵树了。”
“可我还是个处男啊。”我打趣地说。
她没有笑。
“这方面的奥妙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助理的眼睛一眨一眨,似乎在犹豫措辞,“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想,他们准备开始研究你的生殖方式。”
“不会吧?”我瞪大了眼睛。
其实,依靠植物的触觉,我感觉得到,作为人类男性的特征已经消失,但我仍不死心,“如果中断拟植过程呢?没有逆转的办法了?”
助理颓然摇摇头,“你的身体组织已经完全硬化,正式迈过拟植的分界线,变回人类的几率......可以说,相当渺茫。”
我早已心灰意冷,但从专业人员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仍然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我不明白,我只是接种过橡树苗而已,全国该有上亿人跟我一样,偏偏是我变成了一棵真正的橡树,”我有些失望。
“这可能是由于您父亲的原因。”助理轻声说,“您的母亲....跟我们提过。”
“我知道。”我长呼一口气,树冠上的叶子沙沙作响。
这下,轮到助理惊讶了。
“他是研究z射线的人,从小就带我到实验室去,而我长大后变成了一棵独特的橡树,刚好免疫z射线,这里面的缘由总会耐人寻味。”我冷冷地说。
“他是个英雄,”助理出声反驳。
听到这个词,我的树冠忽然垂下去,枝叶吸足了水似的贴在枝桠上,像一只安安静静的石樽。
助理接着说下去,“这是您的母亲交待我的。她说,不希望您记恨自己的父亲,他自杀的原因,正是愧疚于您可能会遭受的痛苦。从后来的证据看,在您被当作实验品之前,超高强度的z射线就已经在实验室泄露了。也就是说,您的父亲也是受害者。”
“因射线病而死,或者选择冒一次险,成为真正的树人。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助理的声音飘飘忽忽,我几乎是在颤抖中听完的。
“不,他是全世界的英雄,却是我一个人的懦夫。”
作为专业人员,教授的确比我想的长远。
我已经完全异化为一棵植物,却不受大气中z射线的影响,仍然在茁壮成长。枝叶上渐渐有了成簇的凸起的结节,那是生殖器官的最初形态。
繁殖出更多的同类,将种子洒满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让地球再次变成绿色的海洋?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让人心动。想来有趣,刚到林场时,我对树人的日子深恶痛绝,如今却全然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人,或者说树,都是善变的生物呀。
我考虑了两天,决定接受教授的授粉计划。
助理们往我的皮肤上插满了电极,开始逐份地试验不同种类的花粉。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步骤却很繁琐。橡树的种类很多,其间的基因差异自然也不小。
每试验一种花粉,都有一大堆数据要分析,一帮人围着我问这问那,一会儿问我思维有没有受到影响,一会儿又问我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老实说,我是真地不知道。那些代表着生命延续的种子碰触到我的身体时,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以橡树的树龄算,也许你还没到性成熟的日子。”最后,教授作了初步推断。
我有些脸红。
母亲辞掉了工作,专程到林场来陪我。
我长的越来越快,枝叶越来越多,树冠越来越繁茂。母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大剪刀,一得空,就帮我修剪枯枝,好让我的眼睛能够显露在外。
我经常问她,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父亲去世时,我还只有四岁,早年的记忆就像冬日里的晨雾,影影绰绰地看不分明。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衬衫?穿多大码的皮鞋?他也跟园丁大叔一样总是剃不净胡茬吗?
“他是个普通人,一个傻瓜,一个时常犹豫的人。但他肯定是一个好人。”母亲说着说着,开始揉眼睛,“今天的风怎么这么大。”
两年后,林场开始了第二轮花粉试验。
虽说,我当初接种的苗种是橡树,但经过z射线的改变,以及我自身基因的融合,在橡树大类里很难找到与之相宜的花粉。
这次,教授找来了更多样本,甚至启用了种子库,培育了许多早已在自然界绝迹的树种。
最终,一种叫作木棉的乔木成功与我搭上了线。
授粉计划看起来很成功,我的枝桠上很快长出了一些淡绿色的小花,像毛毛虫似的短短的,一束连着一束,看起来其貌不扬。
那些天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火炉,全身都滚烫滚烫的,连脑袋都烧的迷迷糊糊。我能感觉得到,我从土壤和营养液里汲取的养分,绝大部分,都透过体内细密的脉络输入到那些小花里。
生殖,果然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几乎就像渴求一位女性的关注一样,渴求那些种子的育成,脑海里空空如也,只剩下那些毛毛虫似的小花。他们是我的全部,全身上下最最重要的东西。
很快,这些毛毛虫的颜色逐渐变深,又慢慢成熟为一个个橡果,直到深化为暗棕色,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在我的感知里,这些橡果变成了无数个殷切的期望,欲发未发,等待最后的释放。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夜。母亲临时外出,教授和助理们也离开了实验室,去和家人们过中秋,这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几乎在一瞬间,我就明白,身体里蓄谋已久的某个时刻,已经到来。
几个月来沉蓄的力量,在我的身体里疯狂地涌动,想要从身体上的每一个毛孔,或是枝桠上的每一个缝隙里,或是橡果的每一道裂痕里,挣脱出来。
我打了个寒颤,随着树冠一阵剧烈的抖动,橡果们一个个脱离了枝桠,被那份力量猛烈地甩了出去,就像是被我丢出去似的。半空中,那些橡果又在数秒内爆裂开来,将藏在内里的种子抛射出去。
噗...噗...噗.....
转眼内,那些从我身上飞射而出的种子,已经布满了周边数百米的范围。
我累极了。
教授说我活不过五十岁。结果,我生生熬走了他,接着熬走了园丁大叔,枝桠上仍然长出了全新的嫩芽。
十年后,母亲也在我的树荫下离去。
之后呢?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活了多少年。
人们常说,父母是我们的来处,等到父母去世,我们的人生就只剩下归途。这句话的确说的极好。
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忆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母亲去世之前,我用树枝捉弄教授,与助理们插科打诨,活的仍然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后,我的记忆进程陡然加快,所有的事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
那时我长到一百二十米,根系则将半个林场纳入我的版图。我成了世界上的名人,登上各地的报纸,人们争相与我合影,将我的形象做成可爱的手办。数十年来,我的种子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我的后代们拥有挺拔的身躯,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无穷无尽的繁殖能力。没过多久,绿色植物就再一次占据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我却无悲无喜,没有太多特别的感受。
研究我的团队已经换了第五拨,每天都有陌生的面孔来来去去,我已经很少说话,也不再与那些新来的实习生们交流。
直到某一天,新来的助理清理了林场的杂物间,从母亲的遗物中找到了一本泛灰的书,是父亲当年的日记,厚厚的,写得满满当当。
那时我的眼睛被树冠遮住,目力所及的地方只有一片翠绿。
照料我的助理将那本日记读给我听。
她读到父亲手写的一首诗,叫做《致橡树》,是一首已流传两百多年的诗歌,
......
......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足下的土地。
......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