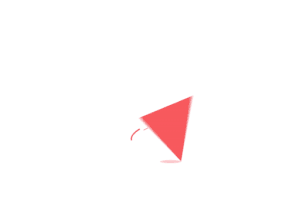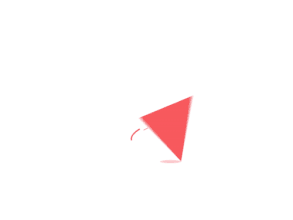吴宝俊:反面教材的反面
这位科普老师不走寻常路。
在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做科学传播很高调的80后,他就是自我戏谑地把“反面教材”作为自己网名的吴宝俊。他的高调不仅反映在做科学传播这个事情上,也体现在他愿意帮助很多希望进入科学传播领域的同侪,实际上这是在建立一种生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所理工科研究型大学的公职身份而言,主要目的在于宣传科学院,宣传各个学科,同时也承担一份社会责任,告诉下一代‘热爱科学才是正道’。”
几年前,就有从事科学传播的学者提出,科学传播已经不再是少数“明星科学家”的保留战场。它是由各种各样的全职传播者(与许多热心的志愿者一起)组成的领域,无论是那些转向全职传播的科学家,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专业传播人士(如公关人员),或是越来越多的经过专业科学传播训练的个体骨干。所以我们需要明星科学家,也需要奋斗在各个领域的积极从事科学传播的其他科学传播人员,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科学传播生态。
报复式嘲讽的“网名”
与80后一代在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崭露头角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热衷于从事或者支持科学传播活动。
在吴宝俊看来,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与80后一代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因为“每一个80后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遇到各种恶俗反智思潮的阻力。也就是冠以各种模式的“读书无用论”,甚至这种论调常常挂在自己的亲属和邻居嘴边。长此以往,会让很多身体跨入高等学府的人产生某种厌学情绪,进而错失了自我提升的大好时光。而在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过程中,很多人开始幡然醒悟,发现了科学的重要性,但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正是在反思这种思潮有害的背景下,很多80后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支持科学传播工作。吴宝俊坦言,他之所以用“反面教材”这个名字,也是一种“略有些小心眼的报复式嘲讽。”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公开的资料去了解他在科学传播方面开展的一些工作,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不应该是科学传播的“反面教材”,因为无论他于公于私都把科学传播当成了一件“事”来认真地对待,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反面教材的反面”。
科学传播的作用是多元的
在《科学与公众:传播、文化与可信性》一书中,简·格雷戈里和史蒂夫·米勒曾经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有9个方面的益处。同时其他研究者也在不同的文献中论述了科学传播也有着多面向的益处,包括宏观的、中观和微观的。而实际上,对于科学传播的实践者而言,虽然对科学传播的益处并没有系统性地总结和梳理,但是他们却能发现很多理论研究无法关注的视角,因而也就可以提出个人旨趣之下的科学传播的益处。
当谈及科学传播的受众时,吴宝俊认为它是针对公众(或者非专业人士)从事的科学传播活动,所以它的作用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虽然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有交集,但是科学传播应该是科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当然他所指代的科学教育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内科学教育。其次是宣传科学家做出的科学工作,实验室里的前沿成果,科学技术转化的产品。因为只有公众理解了科学,他们才可能对科学形成理性的认识,并且支持科学,“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是职业科学家生存的必要保障,从这个角度讲科普也是前沿科技知识的宣传手段。”最后就是科学传播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功能,或者说消遣性作用,“针对大众的科普活动和作品往往需要具备足够的娱乐性才能获取足够的传播度,从这个角度讲,科普是可以作为娱乐活动存在的。”不过,吴宝俊坦言,目前我们还需要就科学与艺术(娱乐)的结合还需要有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也正因为意识到了科学传播的上述作用,吴宝俊在访谈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科学传播对象的理解。“老百姓会为教育内容、科技产品(包括医疗知识和产品)和娱乐内容买单,” 因为“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会使一个人在拥有知识的同时拥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平台,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经济回报;科技产品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和健康状况;娱乐内容满足人内心的情感需要,调节人的情绪状态。”就上述三个方面来说, “如果科学内容脱离了教育,科技产品,以及娱乐,而单独存在,我实在想不出老百姓为什么会为它掏腰包,因而我认为此时它就脱离了市场,而变得不受欢迎。”
科学传播环境需要媒体记者和科学家共同塑造
我们常说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当然这里的公众指的是完成了或者离开了正规教育的那些人,因为离开了正规的教育环境之后,很多人就几乎没有机会去阅读“真正的”科学文献,甚至可以认为,文理分科导致了很多“理科生人文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文科生则从16岁起就彻底告别了牛顿,科学素养普遍偏低。”所以,作为科学传播“二传手”的媒体就需要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传播到受众手中的科学不会扭曲或者被噪声所干扰。
同时,在吴宝俊看来,当前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文科生,而与此同时,媒体从业人员又是信息媒介的介导者,他们决定了公众能从媒体渠道中获取怎样的信息和知识。”所以吴宝俊说,这种实践导致的一种可能悖论就是:
科学从业者的表达能力并没有大家期待中的那么好,而媒体从业者却又会在制作传媒内容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内容重新进行加工,比如,在制作科学节目时,编导和后期剪辑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专家解读的话进行删改,把听不懂的学术名词删掉,剩下的话拼接起来;在进行科学采访时,记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把科学家的话重新表述,这最终导致一个雪上加霜的结果:硬核的科学知识很难出现在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上,即便出现,也往往是被剪辑删改得面目全非以后的结果,失去了原本连贯的逻辑,变得更不容易被观众理解或更容易被观众误解;纸媒对科学家进行的采访报道,也经常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科学家对此叫苦不迭。
而欲改变这种现状,则需要科学家与媒体记者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改善二者的关系,用吴宝俊的话说就是二者的合作要“再深入一些”,具体而言,“科学家在制作节目时,千万不要录制完就不管了,还应该介入片子的剪辑过程中,帮助编导理解消化自己提供的科学内容,并对最终的成片进行审片,科学家在接受纸媒采访时也不要聊完就不管了,最好能够对记者写成的采访稿进行把控,帮助记者修改文字中的科学表述,这样才能保证向公众推送的科学内容是没有被断章取义的。”
实践出真知
我们都知道,科学传播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事情,所以好的科学传播方法一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同时也可以从具体实践中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于吴宝俊而言,他从一个实际工作参与者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先要进行大量的实践,要做科普报告,写科普文章,拍科普视频,脱离了实践活动来谈科普理论,就如同脱离了小剧场演出来谈相声理论一样,失去了根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很多从事科学传播研究的人在对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很多有益于开展科学传播实践的成果和建设性意见,只不过这些成果首先仍然出现在学术期刊中,但是对于实践者来说,他们很少去查阅文献,所以这又是一个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论。
吴宝俊对此也是认同的,因为“实践也只是第一步,在实践的同时,还应不断总结经验,去琢磨自己的作品哪个地方不够好,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而且他也注意到同行交流的重要性,“琢磨也只是第二步,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还应多和合作者,科普同行,以及媒体朋友交流,把自己总结的经验灌输给他们,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和你一起琢磨,发生人传人的迹象,这样就能把圈子带起来,大家共同得到进步。”实际上,他这里表达的也同样是用方法来指导实践,只不过这种方法并未上升到某种程度的理论层次而已。
“长路漫漫”的生态建设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很多本职是科研工作的人在从事科学传播时往往会面临一些窘境,究其原因在于科学传播还没有被正式地纳入到考核之中。“我们每个人和自己所在的单位都签了工作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了我们工作的范畴和职责,这是我们考核晋升的基础。科学家和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是科学研究和教学,所以考核晋升的基础就是科研和教学。”或者换句话说,科学传播并未被写入到合同中规定的工作范畴,所以“如果一个科学家或大学教师希望用科普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声望来实现考评考核的优秀和职称的晋升,那么他一定会遇到阻力,否则对其他的同事不公平。”
恰恰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吴宝俊觉得可以考虑把“科学传播工作写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合同,真正成为科学家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样可以解决一些眼前的尴尬。”同时,他也认为科学传播的生态建设很重要,但是这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方面需要科学家和媒体学会如何正确地做科学传播,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科学家慢慢地熟悉起科学传播这项新的技能,因为就当前的情形来说,让所有科学家都去参与科学传播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用吴宝俊的话来说就是“恐怕还没到时候”。
本文图片均由吴宝俊老师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