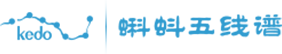探视
我怕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让我慢慢体会。
王菲:《童》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
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余华:《<活着>麦田新版自序》
天快黑的时候,那个老人来了。
A
我最近总是想起过去的事情,过去我年轻,健康,不像现在。现在,我只能躺在床上,身体被各种机器饲养着,它们成了我身体的外延,是我的心肺。说起来,我的年龄并不算大,起码不算老,我今年54岁。54岁在2000年就属于晚年了,但在2040年顶多算是中年。人们通过各种养生手段,拉长了生命线。许多跟我一样年龄的人们,看起来朝气蓬勃活力十足,他们远足、郊游、爬山、骑行,完全不输年轻人。可我只能躺在床上,被病魔蚕食。
我想起50岁那年春天,在健身房,我活泼得不像话,我可以在跑步机上连续运动半个小时,气息均匀。从去年开始,儿子为我办了小区健身房的年卡,他跟我说:您要多做些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我收下了他的孝顺,只要时间充裕,我就过去健身。是的,我时间绝对充裕,一个年近半百之人,一个电力公司的普通会计,一个早早失去丈夫的独身妇女,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那天天气很好,真得很好,我一生之中都没有看见过几次这么漂亮湛蓝的天空,这让我心情舒朗,想要像个少女那样跟一朵花一只鸟打招呼。我来到公司,陷入熟悉的格局和环境,没有任何过渡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之中:整合,计算,制表。我熟练地梳理着工作内容,没有兴奋点,也没有困扰项。
午饭时,我端着餐盘找位置,看见人事的胡姐对面是个空位,但我可不想跟她同桌,无奈她看见了我,伸手招呼道:“林云,这儿,这儿。”
我躲不过去,只好微笑颔首。
“上次给你介绍那个怎么样,联系着没有?”胡姐说。我就知道她会这么问。
“那个工程师啊,他总是出差,我们之后就见了一面,他还接了一个电话匆匆从餐厅离开,也没个解释,我觉得可能是看不上我吧。这回可不是我的原因,我挺积极争取了,这次是人家看不上我。”我说了一堆,把自己择干净。
“打住,”胡姐说,“上次给你介绍那个是一个报社编辑。我可是听人家说,给你发信息总是不回复,回复也只是敷衍。”
“哦,哦,那个啊。”我打着哈哈,“那个人家品味太高,初次见面就带我去听音乐会,我就听过音乐,别的不会啊。”
“听音乐会那次,你中途退场了吧。”
“没办法,我就是一个俗人。”
“司法厅办公室主任那次约你听得音乐会。”
好吧,我完全搞混了。怪我,全都怪我。我既然不愿意再嫁,又何必闷着头子相亲。相亲之后,又要处心积虑地搞砸。是爱情作祟,是回忆叫嚣,还是习惯使然,我说不清楚。我也劝过自己,刚开始丈夫去世,我把自己的世界全部倾斜给儿子,现在儿子长大了,离开我了,有了他自己的天地,我可以摆正自己的心态,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所有人都会理解我的选择,支持我再找一个,人老了,好作伴。可不知为什么,见面之前,我一鼓作气,见面之后,我就三而竭了。
“对不起,胡姐。”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人家,也对不起家人。你儿子可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帮你惦记着。”
“他说什么了?”我问道。儿子工作很忙,我们母子的沟通和见面日趋减少,因此跟他相关的信息,我总是渴望全面了解和吸收。
“他说,要我为你找个老伴。”
“他都一个人,我着什么急?就是胡姐,你别老盯着我,你也帮我儿子物色一个好姑娘,这是正经事。”
“拉倒吧,你儿子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介绍。”
这倒是。
儿子大学学得物理,量子传输什么的,具体我说不上来,硕士、博士,一直连读下去。有一天,他突然回家,跟我说要离开一段时间,我问他去哪儿,他神秘地说,国家征调。从此之后,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如果不是他时不时打来一个电话,或者回一趟家,我真以为他遭遇不测。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我吃了一口饭,说。
“没有。”胡姐说,“你不会自己跟他打电话啊?”
“我不想打扰他。”
“你说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多不容易,辛辛苦苦把那些小崽子们从小拉扯大,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他们离开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再想见他们一面,就跟求他们似的。你说我们当父母的,为了什么?谁指望他们养老,只不过想在老的时候,能够见见他们罢了。”
“都是这样,我们不也是这样疏远了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会被自己的孩子放逐。这就是生活。”
“说得真好。”胡姐说,“这次这个你们一定能说得着,别说我不照顾你,这次给你介绍的可是一个大作家,出过好些本书。我给你讲下基本情况,今年58岁,离异,工作说了,是个作家,收入不详,但肯定低不了,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人好,我可听说了,这个作家特善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悲悯。”
“那怎么还离婚了?”我问。
“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如今作家跟艺人一样,不离几次婚,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混娱乐圈?”胡姐高谈阔论道,“怎么样,见不见?你要是不见,以后就别想让我管你这摊子破事儿。”
“见,我见还不行吗?”
我俩相视一笑,为这个谐音感到尴尬又欢乐,我的心情在那一瞬间跟天气一样好。
B
我很快跟那个作家见了一面。
“您好,我叫李超。”
“您好,我叫林云。”
“胡姐搞错了吧,我是找二婚的,您这也太年轻了吧。”
“你们作家都这么能说会道吗?”
我的几次相亲经历,沉闷都是主色调,李超的幽默让我们很快打开局面。毕竟,我们不比年轻人,他们还有大把时光,可以消磨,可以虚掷,我们必须一针见血。
我们彼此投缘,聊得风生水起,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是蛮有文艺细胞。我们谈到阅读,他说:“我这辈子,做得最不亏的事就是阅读。你想想啊,一个作者呕心沥血一年半载,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写出来一部小说,我们只用几天时间就可以读完,也就是说,我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能够经历他的一生,这还不够划算吗?”
说来惭愧,我很少阅读,青年时代倒是笼统看过一些世界名著,也曾在大学加入文学社,有过一些涂鸦之作。参加工作之后,结婚之后,生了儿子之后,我的精力和注意力都被抢劫,阅读成为一种奢侈。而现在,我有的是时间。
我们还聊到注意力。
他说:“注意力这个问题,我有些思考。我以前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去翻翻手机,看看我上午发在社交软件上的信息有没有读者回复,朋友圈有没有新动态。因此,总是写写停停,一天下来,码不了两千字。总是渴望外界的介入,总是担心别人的看法,就是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而在他人那里,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够好。你看那些伟大的人们,谁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呢?他知道自己是伟大的,这就够了。所以说,远离他们,才能找回自己。”
“是啊,我们都不是伟人。”
“能做到专注真的很难。”
“那你后来怎么做到的?怎么克服的诱惑?”
“很遗憾,我没能克服诱惑,我是没有诱惑了。某天早上醒来,突然就明白了时间的有限而金贵,好的作品却层出不穷和应接不暇,它们垄断了我的注意力。”他喝了一口咖啡,“我还有一个话题想说,初次见面说这些可能显得有些不合适,你听听就好,随时可以叫停。我想说的是关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你认为这是一种什么关系?”
“互补的关系吧?我不知道,我看书不多。”
“那我直接说我的看法,我一直认为作者和读者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关系。我这么说并不是妄自尊大,看不起读者。完全没有。我非常尊重我的读者。事实上,我根本做不到这样,所以才会特别在意读者的反应,还会根据他们的反应去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现在阅读式微,出版式微,人们的阅读都集中在客户端。我发现,读者不愿意看复杂的东西,不愿意思考,他们渴望简单直接。我看过一些食之无味的空洞文章,却备受读者推崇,评论里总说看哭了之类。往往,我不用构思,随手扯一个短篇,能有不错反响;我静下心来,谋篇布局,传达观点,丰富人物,读者就意兴阑珊。甚至好多人直言,不好看,看不懂。我不是说这是读者错,这是时代的错。也不是时代的错,而是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冲突与症结。所以网络文学活了,传统文学萎了,青春文学活了,纪实文学死了。当然,当然写作者要从自身寻求突破,不能像怨妇一样指摘。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家,每每出书都能掀起热潮,引起轰动。比如前些年的刘震云。刘震云就曾经评判过这类文学。大意是说,很多文章只能叫文字,不能叫文学,从文字到文学还有20里路。对不起,你看我,一说到这些就有些忘乎所以。”
“没有,我很喜欢听。”是真的,并不恭维,他高谈阔论的样子,有一种成熟的可爱。
我在咖啡厅吃了些点心,因此免去了晚餐,稍微有些东西垫底就好。
告别李超,我直接去了小区的健身房,我在那里有自己的柜子,里面有松垮的运动衣裤。我做不到年轻人那样,穿着勾勒身材的紧身衣健身,毕竟,我已经50岁了。
我用慢跑热身,然后玩了一些器械,心血来潮,我找来哑铃握举。先是左手,很好地完成一组十个的动作,换右手,一个,两个,在做第三个的时候,我感到右肩到右臂一阵发沉和酸胀,哑铃从手里脱落,砸在地上,索性没有伤到脚。我当时没有在意,还为自己的失手感到抱歉。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我对自己说。我来到洗澡间,打开淋浴。我轻轻地抬起右臂,绕着肩部转圈,疼痛再次袭来。我仍没有当回事,心想可能是昨夜睡觉压迫的。我打了沐浴露,在身上涂抹着,然后就摸到了乳房上的上僵硬的、蚕豆大小的肿块。
不疼,一点都不疼,可我心里却咯噔一下,像失重一样,感到一阵空虚,几欲摔倒。
我走路回家,月光皎洁,路面泛着一层银光,如地上霜,在这不可多得的好天气里,我再也快活不起来。
我很想给儿子打个电话,思前想后,我却打给了父母。
父母尚在,不敢言老。
母亲听完我的讲述,强烈建议我明天就去医院检查,我说等周末吧。
不曾想,第二天一早父母就赶到我家(他们有我家大门的钥匙),把我从梦中叫醒,从床上拽下来。
“快点收拾东西,去医院。”母亲命令道。
“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我嘟囔着,像个孩子。
“什么至于不至于,女人的事儿,我比你懂。”她这话让我这个中年妇女无地自容。
我几乎是被他们老两口押到医院,我尽量表现得无所谓,并责备他们的大惊小怪,其实我心里根本没底,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手心湿漉漉的全是汗。
父亲说,不会有事的。我也这么安慰自己,不会有事的。
医生却不这么认为。
“乳腺癌。”他说得很平静,就好像是说,感冒,发烧,咳嗽,头痛。
C
“想什么呢?”李超递给我一个削好的苹果。
“没什么,一些陈年往事。”我接过来,浅浅咬了一口。
“有没有想到我?”
“还真有。”
“我以为你就会想你的宝贝儿子。”
“想他有什么用?又不会来看我。”
“我有预感,他今天会来探望你。”
“我也有预感,你的预感会落空。”
以上对话发生在我53岁,乳腺癌确认后第三年,我住进了医院。我已经度过了刚确诊那段时间的茫然和痛苦,坦然接受这样的命运。不接受又能怎样呢?我们不比年轻人。50岁懂得浪漫,更懂得现实。几天之后,我接到李超的电话,他约我看电影。我拒绝了他。
“为什么?”他似乎觉得不解,认为我没有说不的理由。
“不为什么。”我当时正值黑暗的低谷。
“我需要一个可以说服我的原因。”
“我被确诊为乳腺癌,这个原因可以说服你吗?”
“你现在不需要呼吸机吧,也不用化疗吧,那为什么不能继续享受生活呢?你只是得了癌症,并不是立即执行死刑。正因为时日无多,你别嫌我说话难听,才要更加心无牵挂地去快活。告诉你们家地址,我开车过去接你。”
就这样,这些年李超一直陪着我,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关系,大概只能是朋友。别人问起,我也这么介绍他。父母已经年迈,儿子忙于实验,他连恋爱都没时间去谈,我怎么忍心分散他的精力。父母都是这样吧,都觉得自己对孩子的付出不够多。他们的事情再小也重要,比如跟同学聚会,比如去看球赛,我们的事情再重要也小,比如身患重疾,比如孤苦伶仃。跟随时都可能剥削掉我的余生的癌症相比,一个人的寂寞更加难熬。我多想能够时常见到他。
我还想起他两三岁,已经能够清晰地说话,浅显地表达,他总是不安生,睡醒就到处乱跑,除了睡觉,他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我那时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帮我看孩子。只要我下班,他就会长在我身上,任谁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否则他就要嚎啕大哭——那是他控诉的方法。他是真得离不开我。现在呢,他是真得离不开工作。我理解他对研究的热爱,他从小就喜欢拆解和组装玩具,但他是否理解一个母亲,一个生命垂危的母亲,想要时不时见到自己唯一的孩子的需求?
那天,他没有来。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儿子跟李超打过电话,说会来探望我,临走,实验出了问题,不得不留下来。
“实验远比我重要。”我有些赌气。
“当然比你重要,”李超还在帮我儿子说话,“他的实验是利在千秋,造福全人类的,你能跟全人类相提并论吗?”
“全人类他也就我这一个妈。”
“这倒是。”
“给他打个电话。”
“说什么呢?”
“就说——算了吧,我不是那种锱铢必较的人。”
我没有想到(谁也不会想到),那天我们母子没有见面,再见面已是一年后,我的弥留之际。
D
情况在上礼拜开始恶化。
疼痛从乳房开始,向全身游走、蔓延,我几次失去知觉。
我浑浑噩噩地活着,不辩黑夜白日,我残存的一些意识,想的都是儿子。他到底在忙什么呢?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开始我不断问过他,旁敲侧击,他最多说到两个字:机密。我不知道,他一个物理学博士为什么会去到部队上,又怎么涉及到机密,一年一年地被我们老百姓触摸不到的高层牵绊在某个连番号都不能泄露的驻地。这哪里是做研究,分明是住监狱。他今年已经30岁了。
我以前从电视剧里看到那些处心积虑想要给女儿找到伴侣的父母,总觉得他们有些矫枉过正,等到我也成为那样的父母,终于体会到他们的良苦用心。我们谁都知道,看到他们交到男(女)朋友,并不能等同于幸福人生,但就是会感到心里宽慰,尤其是在弥留之际。
在度过了漫长而反复的短暂醒来和沉重昏迷交迭期后,我迎来了一阵难得的舒适。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李超还跟我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实际上,哪儿是什么大难不死,而是凛冬将至,风雨欲来之前的平静。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说道,竟不怎么吃力。
“在所不辞。”
“我死之后,我儿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你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下我的葬礼。简单一点就行,我不要放哀乐,我要放音乐,舒缓一点的曲目都行,钢琴曲或者流行歌曲都行。”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现在是考虑出院后去哪里游玩的时候。”
“拜托你了。”
“死亡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残忍不在于终止生命,而在于造成永别。”
“其实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对于这不算漫长,也不短暂的一生感到非常知足,虽然我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失去了爸爸,我失去了爱人,虽然一个人抚养孩子历尽了辛苦和委屈,虽然儿子跑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活着,虽然有那么多虽然,但是我还是要说但是,至少我有过一次生命旅程。”
“你心态真好。”
“不然怎么样?”
“真不知道我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李超有些黯然,好像将死之人是他。
我活了一辈子(不管多久,到死都是一辈子),发现一个真理,跟你交心的朋友一两个就够了,三个就多了。在我生命的尾声,能交到李超这样的朋友,也算死得其所。
“别这样嘛,你们当作家的,对生老病死应该比一般人接触地多。对了,你如果有时间,请把我们之间这两年的相处写一篇文章。你之前借给我严歌苓的《床畔》,讲一个细心的护士照顾植物人伤员的故事,你也可以讲讲你照顾我的经历。”
“我写,我一定写。”
“那到时候发表了,别忘了给我寄稿费。”死亡本来就是一件沉重的枷锁,我们何不乐观一些面对。面对我们无法扭转的局势,一味沉沦又有什么好处呢?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阵猛烈的脚步声,须臾,我儿子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病房门口。
他冲刺到我的床前,跪在床边,双手紧紧握着我枯瘦的手,两眼噙满泪花,“妈妈。”
无需多言,我要得就是这两个字而已。
“你终于来了。”我用另一只自由的手摸着他的头发。我们大概有两年没有见面,他看上去却沧桑非常,他今年30岁,看上去却像40岁,黑发中间杂着丝丝白发。
“我终于来了。”
“你们聊,我出去抽根烟。”李超站起来,腾出我们母子相聚的空间。
“没关系,你在这里。你不是还要写我的故事吗?我的故事里不能没有我的儿子。”我坚持道。
“您是?”儿子看着李超疑惑。
“这是你李超叔叔,妈妈患病这几年,都是他陪着我,忙前忙后。”
“谢谢您。”儿子对李超说。
“没什么。”他不以为然道。
“妈,孩儿来看您了。”儿子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刚说完这一句就泪眼滂沱,涕泪横流,他哭得那么伤心、认真、用力、忘我,就好像——好像我已经死了。
“来了就好。”弄得我只好安慰他。
“请您原谅我这些年的不孝,没能在您身边伺候。”
“母子之间,哪里有什么原谅不原谅。国家比我更需要你。”我说。最后一句听起来有些像是气话,希望他不要介意,这不过是我这个当母亲的一点抱怨和哀伤。
李超出去买了些吃的,我们三个人在病房简单凑合了晚饭。吃完饭,李超起身告辞,房间只剩下我和儿子。他重新变得像小时候那样,像长在我身上那样,形影不离。这一刻的陪伴,就弥补了多年的空白。做父母的就是这么容易满足,就像当年我们用一块糖果,一只足球就能让孩子欢天喜地一样。
吃完饭,我还觉得身体状态不错,跟儿子浅浅地聊着天,说到他小时候的淘气,上高爬低,总是让我担惊受怕,终于在他五岁那年,他上树掏鸟窝,从树上面摔下来。他的胳膊剌了一道大口子,血像自来水一样往外流。当时是夏天,我脱了T恤包裹着他的胳膊,顾不上回家,就这么穿着内衣抱着他打车去了就近的医院。当妈妈的总是容易放大孩子受的伤,我以为他要截肢,事实上,只是缝了几针,并没上到骨头。他哇哇大哭,边哭边说:“妈妈骗人,树上根本没有鸟窝。”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休息一下,接着说:“说句不好听的,我怕是没有机会看到你结婚生子了,这不能说不遗憾。”
“妈妈。”
说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然后我就感觉到呼吸困难,儿子站在床边,并没有急于帮我去叫护士,他只是静静端详着我。
也许是错觉,我看到他逐渐变得透明,我看见他掏出手机,手机也变得透明。我还看到他身后的门被护士撞开(根据我身体的参数,另有一套报警系统吧),她们穿过我的儿子汹涌地扑在我的身上进行抢救。
我知道,我要死了。
E
“我写,我一定写。”
“那到时候发表了,别忘了给我寄稿费。”死亡本来就是一件沉重的枷锁,我们何不乐观一些面对。面对我们无法扭转的局势,一味沉沦又有什么好处呢?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阵猛烈的脚步声,须臾,我儿子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病房门口。
他冲刺到我的床前,跪在床边,双手紧紧握着我枯瘦的手,两眼噙满泪花,“妈妈。”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没有电话通知,也没有托人告诉,不过,一个儿子看望他生命垂危的母亲,需要什么告知呢。他来就是了。
我永远等待他。
“李超叔叔您好。”他转身对李超说。
我并没有印象介绍过他俩认识,事实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这些年,我跟儿子第一次见面。也许是胡姐说的吧。
“你好。”李超站起来说,“你们俩聊,我出去抽根烟。”
“没关系,”儿子说,“感谢您这几年一直照顾我妈妈。”
“没什么,没什么。”
这么一来,我确定就是胡姐告诉我儿子,我跟李超的关系。不知道她会怎么说,会不会用到朋友之外的词汇。
“妈妈,”儿子握紧了我的手,“您知道这十几年我有多想你吗?”
“妈妈还没糊涂,你先糊涂了,上次见面到现在不过三四年啊。”我笑着说。
“对对,是是,我太激动了,也太开心了,能看见你。”他有些语无伦次,看上去比我还要高兴。他怎么能比我更高兴呢?
“我有好多话想对您说,可是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妈妈,”他动情地流出了眼泪,“就让我在您怀里哭一会吧,像小时候那样。”
“我还是出去吧,去买点吃的。”李超站起来说。
“也好。”
李超离开之后,我问儿子:“你这些年过得并不好吧?你看你,跟你走得时候判若两人,那时候你风华正茂,现在怎么这么沧桑呢。”
“实验比较辛苦,这是外因。我对您的思念,这是根本。”
“回来就好。”
晚上我们一起在病房对付了晚饭,李超起身告辞,剩下我和儿子两个人。
“您还记得我五岁那年,上树掏鸟窝那次吗?”儿子突然说起这件事。
“当然,我怎么会忘记。你问我,小鸟在天上飞累了怎么办?我就说,回到它们的窝里啊。你又问我,它们的窝在哪里?”
“您告诉我在树上,还说所有的树上都有鸟窝,那是它们的停泊的港湾。”
“你从树上摔下来,我当时都傻了,真害怕失去你。可我终究要失去你。每个父母都在孩子长大之后失去了他们。”
“我也会失去我的孩子吗?真不敢想象,这些年我都对您做了什么?不,我什么也没对您做。”
“等你有孩子你就会明白了。”
“妈妈,我去年就结婚了,她现在已经怀孕。”
“真的?这么大的喜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妈妈?”
“是的,这是真的。”
“你该不会是哄我开心吧?”我敏锐地察觉到什么。
“当然不是,有机会我带他们来看您。”
“没机会了。”我自嘲道。
这时,儿子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妈妈,再见。”
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感到一阵头晕,病魔开始了疯狂地反噬。
F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现在是考虑出院后去哪里游玩的时候。”
“拜托你了。”
李超有些黯然,好像将死之人是他。
这时,我听见敲门声,抬头却发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有些熟悉的陌生人。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他,可是他是谁呢?
“您好,请问您找谁?”李超站起来问道。
“是我啊,是我啊。”他走过来,含着泪花,哽咽着说。
“儿子?”我难道是在梦中,还是产生了幻觉,眼前这个人怎么看也有五十岁上下,可他的眼睛眉毛,分明就是沧桑之后的儿子。
“这怎么可能?”我和李超异口同声。
他没有说话,只是挽起来衣袖,露出胳膊上一条长长的疤痕。
H
天快黑的时候,那个老人来了。
他至少有90岁,考虑到现在人们对于养生的热衷,他极有可能已经过百。他的头发全白了,眉毛也白了,如果他留着胡子,也一定是花白的,穿上红绸外套,就是圣诞老人。我觉得他比我更需要躺在床上疗养。
他颤颤巍巍地走进来,李超连忙上前扶住他,顺便问道:“您找谁?”
“我能在这儿坐坐吗?”他一边征求意见,一边已经坐在床沿上。看来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
“您是迷路了吗?”李超问道。
“没有,我怎么会忘记来这里的路,这半个世纪以来,我每年都会来这里。”他说道。
李超背着老人对我做了一个动作,用手指了指太阳穴,意思在说,老人这里有些问题。我挥挥手,示意他别这样。我们迟早都会有那一天(我是没有了),有什么权利对自己无法逃脱的命运指手画脚呢?就比如说,我很讨厌一句话,年轻就是资本。还有很多混淆视听的广告语和文章怂恿这些年轻人去勇敢地犯错,不要辜负青春。年轻算什么资本呢?一茬一茬的人长上来,总有人比你年轻。这不是资本,见识、学问、明辨是非的能力、勇于担当的责任心,这才是资本。
我想,这个老人一定跟我一样,都是被儿女漂流在孤岛上的“弃婴”。
不管我们怎么问询,老人都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只是说坐一坐。
我今天难得身体舒服,也有胃口,便让李超出去买了一些东西(我厌倦了医院惨淡伙食的油水),顺便也给老人带些吃的,看来他一时半会不会离开。我当然可以呼叫护士,然后让她们把他“请走”,他也在这里住院吧,说不定陪护的家人已经着急了。我突然有点恶趣味,就让那些孝顺的儿女们煎熬煎熬吧。
“这种感觉真奇怪,”他突然开口了,“当我看着你,心里涌上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一种是儿女对父母的抱歉,一种是父母对儿女的释然。”
他说这话也有些奇怪。
“像您这么大,孙子孙女都有一堆了吧。”我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只好另起炉灶。
“是,是,两个孙子,一个孙女,还有两个外孙和两个外孙女。另外还有,”他想了想说,“一堆重孙。”
“真好,四世同堂,天伦之乐啊。”儿女成行,子孙满堂的感觉真好。我多羡慕他。跟他相比,我算是一个孤家寡人了,唯一的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你在哪里?
“其实已经五世同堂了,很多重孙都已经组建家庭,有了新生命。但是今天,这一刻,应该是六世同堂。”
“六世?”我说。看来李超猜测得没错,老人的确有些问题。就算20岁一代人,六世也需要120年,老人总不至于120岁吧。
“您得的是癌症吧?”他没有顾及我的猜疑,突然问道。
“乳腺癌。”我直言不讳,通过刚才的对话,我们仿佛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
“真可惜,再过20年,癌症的治疗就不在话下。”
“是,是。”没跑了,老人的信口开河只能说明他的确有些精神问题。我想到。
“您一定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吧?来,您来猜猜我多大了?”
“别再称呼您了,我可担当不起。”我说,“您今年有90高寿?”
“少。”
“九十——三?”
“少?”
“九十——”
“早就过了一百岁了。您真得认不出我吗?”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刚才进来被他的苍老混淆,没有细致打量他,仔细看来,他的眉眼间的确有些熟悉的纹路。
不,怎么可能?
不可能。
“林云,”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的母亲。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来探视您了。”
“你叫我什么?”
“妈妈!”他握住我的枯竭的双手,激动地说。
林云在那天晚上病情突然恶化,没能抢救过来。李超感到内心深处,有一些什么东西悄悄破碎了。这些年,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一种超越友情接近爱情的感情。第二天一早,有人敲响他的家门,打开之后,竟然是昨天那个老人。
“我方便进来吗?或者,我们出去找个地方,我知道你很喜欢去一个咖啡厅。我看了那本你写得照顾我母亲的书。”
“你在说什么?”李超昨夜一宿没睡,刚合上眼就被他吵醒,心里正不舒服。但更多是惊讶,那本书的构思只有他跟林云知道,而且,还只是个构思。
“李超叔叔,”老人说,“这么叫还真是别扭——我是林云的儿子呵。”
李超写过很多小说,对马克·吐温一句名言深信不疑,大意是说:现实生活往往比文学作品更荒诞,因为后者起码是逻辑的产物,前者却毫无逻辑可循。但眼前这荒诞有些超出认知。
李超一路上仍不能相信,但老人不管从哪个方面试探都无懈可击。老人告诉他,这一切跟他当年(也就是现在)从事的职业有关。简单来说,他不断从未来穿越回来,只是为了见到林云临终一面。
“在我的世界里,我没能赶回来。”老人说,“母亲死后半年,我才获准回家,但我只能为她烧一炷香。”
他们在一家咖啡厅坐下。
李超相信了老人的理论,他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一旦承认这个事实,李超就放松下来。
“这家咖啡厅,就是我当年跟你母亲相亲那家。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愉快的开端。”
“谢谢您这些年对我母亲的照顾。”
“其实是相对的,我的意思是,我照顾了你的母亲,我也活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和充实,这么多年,能说上话、说到一起的人真不多。”李超说,“先别说我,说说你。你是说,你跟我们处在不同的世界?”
“是的。我从未来穿越那一刻起,就分裂成两个世界,一个是按照原先的轨迹发展,一个就是你们现在的世界。”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更早以前,回到林云确诊之前,更早之前,让她早点检查预防?”
“理论上,出于一种保护机制,我们只能探视将死之人。探视对象死亡之后,我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回到未来。”
“你这个理论有矛盾啊,你说只能探视将死之人,那人死了之后,你就会消失,回到未来。现在,你母亲已经死了,你还在这里啊。”经常写小说的李超敏锐地嗅到了一个Bug。
“有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即可。一是探视之人濒死;另一个是,探视之人濒死。”他缓缓说道。
文字上的游戏,第一个探视之人指的是探视对象,第二个探视之人指的是他自己。
“我知道您在构思一本跟我母亲相关的书,但事实上,我已经看过那本书了。”
“是的,我答应过你母亲,要写写她,写写你早逝的父亲,写写你们母子。我曾经跟你母亲讨论过写作的意义。我还是觉得写作者应该自私一点,没有必要去讨好读者。既然要写,为什么不写一些高尚动人的东西呢?我们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啊。”
“那你想好怎么写了?”
“还没有。作家课里讲文章第一句尤为重要。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比如《百年孤独》,‘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类似的,余华在《活着》里也用过,‘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这种倒叙的手法,有一种历经苦难之后回头看风轻云淡的释然。”
“所以,你想好自己的第一句了吗?”
“是的,昨天看见你那一刻,我就想到了。”
“‘天快黑的时候,那个老人来了。’对,就是这个开头。”
尾声:G
“你心态真好。”
“不然怎么样?”
“真不知道我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李超有些黯然,好像将死之人是他。
我活了一辈子(不管多久,到死都是一辈子),发现一个真理,跟你交心的朋友一两个就够了,三个就多了。在我生命的尾声,能交到李超这样的朋友,也算死得其所。
这时,我听见敲门声,一男一女带着一个可爱机灵的小孩鱼贯而入。
我几乎要从床上跌下来,因为我认出了那个男人,虽然他看上去要比我儿子大很多,但不是他还能是谁?这里面一定存在着奇妙的因果,他会慢慢告诉我,眼下我最关心的是他一手牵着的女人和孩子,这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吗?
儿子拍了拍小孩的后脑勺,“叫奶奶。”
我经历了苦难的一生,可我仍然要说,上天待我不薄,眼前这一刻抵得过所有不幸的遭遇。
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