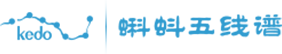白骨夫人
唐僧大惊道:“悟空,这个人才死了,怎么就化作一堆骷髅?”行者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
——吴承恩《西游记》
1
世界是一口棺材,缚住我,也缠住黑暗。
我不知自己在这棺材中待了多久。自我醒来时,这棺材便严丝合缝地贴在我身上。棺木不知是用什么制的,像花灯外的衬布,有些微暖意和弹性。后脑勺处的棺材板破了洞,料峭的夜风像刀子一样捅进来,又随着抬棺人的脚步上下颠簸,激得人浑身发麻。
谢长安曾说,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便敛住了鼻息,如一具真正的尸体那般躺着,直至他们终于停了下来,将我扔到了地上。
“检查下,别留活口。”
“都凉透了!”另一人似是懒得开袋验尸,隔着棺材板探了下我的鼻息,“你看,没气了。”
下命令的人不再说话。没过多久,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两人的脚步声逐渐远了。
万籁重归寂静。
我小心翼翼地在身侧摸索,觅到一处一指宽的缝隙。缝隙不大,韧性很足,我拉扯半天,总算破开一个掌余宽的缺口,钻了出来。
然后,我看到了自己的身躯。
或许那已不能被称作身躯,而是一团被翠衫湘裙簇拥的人皮,鲜血汩汩地往外冒,玉镂步摇斜插于青丝,珠串轻晃。
我心头猛地一跳,缓缓低头,白森森的趾骨、髌骨、股骨、骨盆依次闯入眼帘。
我突然意识到,那棺材木原来是我的身躯。
是我刨开了她的肌理,吐出了她的五脏,破肤而出。
我变成了自己的骨架。
2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十二时辰如砂砾从我的生命划过,太阳像上元节的花灯一点点飘远,飘近,又飘远。我守着自己的身体,边打哆嗦边把自己的关节搓得噼啪响。莹莹绿火从我身上升起,映出乱葬岗上交替重叠的尸首,老弱妇孺,蚊蝇盘绕。
尸体很多,骷髅却只有我一个。
我心里瘆得慌,鼻腔发酸,眼眶发涩,可失去了身躯,我连眼泪都挤不出。
一声暴呵从天而降,“呔!妖精!”
举着铁棍的瘦和尚砰一下在我脚边砸出一个半米深的深坑,棍风猎猎,将我整个震翻在地。我哪还有什么伤春悲秋的心情,连滚带爬地逃出老远。
瘦和尚旁的僧人呵斥道,“悟空,不得无礼。”
一点威慑力都没有。
尖嘴猴腮的和尚却收了手。
我这才得空打量这一行人。僧人,小道士,以及三个嘴脸凶顽的徒弟和一匹白马。
“贫僧管教无方,让你受惊了。”僧人朝我伸出了手。
我不敢握,只盯着他不说话。
僧人叹了口气,给身后那个着青色道服的双髻小道士让了位。
小道士拂尘一佛,双手作揖向我行礼,“在下乃镇元大仙门下弟子明月——”
我再退了两步。小神仙也是神仙。神仙下凡,不图降妖除魔,就为超度亡魂。可是我不是妖,我也没有死。
“你不是妖,你也没有死。”明月顿了顿,补充道:“我也不是神仙。”
我惊讶地看向明月。
“我又不是第一次遇到新生的骨人。”明月骄傲地说道,他的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不过,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有意思,你脊柱上的字是专门找人刻上去的吗?”
我不吭声。
“你知道骨人吗?”
我保持沉默。
他挠挠头,顿了顿,试探着问我:“那你知道,人是共生之物吗?”
3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
先是我莫名其妙成了一具骨架,再是被一个给唐三藏师徒送行的小道士拉着,非要给我起新名字,说我的骨头是他见过最白的,所以唤作白骨。还给我说什么人不是人,而是脑袋和骨头合体之物。
他说,共生是天地间最自然的事。璅蛣和豆蟹都以蛣为食,璅蛣无法动弹,豆蟹没有硬甲,两者共生,豆蟹便成了璅蛣的移动胃囊,璅蛣也成了豆蟹的盔甲。这叫做璅蛣腹蟹。水母没有耳目无法避人,虾难以捕到足够的食物,两者共生,水母为虾提供食物,虾则带着水母逃之夭夭,这叫做水母目虾。
他说,人呢,也没什么异同。人类自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事实上,人类不过是骨人和脑人的共生之物。脑人空有智识慧根,却无骨无足,便如那海中水母,人人得以食之。而骨人无肉无皮,坚若磐石,却不能化天地精华为己用。于是脑人和骨人以肉为墙,以骨为干,共生为人。这是人类的起源。
我觉得小道士纯属瞎扯,却又找不出他言语的漏洞,只得任他在我耳边叨叨。
他耐心倒好,送别了唐三藏师徒便蹲在我身侧,苦口婆心地劝,“你看那唐三藏,他的骨人跟了脑人十代,不也想通了吗?”
我捂着耳骨不想听。
我明明还记得阿娘教我编出第一盏花灯时的温暖笑意;记得谢长安在上元节的惊鸿一箭,最顶上的蝴蝶花灯随风蹁跹,坠入我的手心;记得阿娘病故,谢长安握着阿娘的手允诺娶我为妻;记得新婚夜谢长安按习俗在我背上镌刻的“谢氏夫人”字样。
这十六载人生的每一段旅程,都如此真实分明,像花灯上的绣花,一针针缝入了我的骨肉。但明月却说,这一切都只属于那唤作顾瑶,顾夫人的脑人。而我,骨人白骨,我的人生空空荡荡,寸草不生。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呢?”我很是委屈。
明月叹了口气。他将手伸至耳后,一提一拉,他的肌肤便如衣衫般褪去了。他的骷髅眼眶和我一样,一眼就能望到后面的蝶骨。
“白骨,和我回家吧。”明月低声道。
4
明月说的家,是他修炼的道观,五庄观,坐落于万寿山上,松篁一簇,楼阁数层,方圆百里了无人烟。
戴紫金冠,蓄三长须,面色红润的男子接见了我。明月说,这是他的师尊镇元子,是第一位挣脱脑人束缚的骨人前辈。
镇元子很高兴,专程设了宴。全宴只上了一道菜,菜上只一颗婴孩状的果子。
他们唤作人参果。
“黄帝有言,肉为墙,骨为干。但这人参果却不同——”镇元子将我招至桌前,将这人参果如卷轴般展开,往骨架上一铺一捏,便敛成了人形。
“这果子……”我迟疑地问道,“能作人皮?”
镇元子大笑道:“正是。”他手一挥,那人参果便覆在我身。在它裹住骨架的同时,细小的经脉攀上我的骨骼,涌入清泉,引出浊液,我顿觉精神了几分。待到人参果完全贴合骨架后,黛眉黑瞳从肉瘤中生长而出,我朝镜中一看,已有九分顾瑶的神韵。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镇元子捋了捋长须,“你可知,这人参果从何而来?”
我停下轻抚面皮的动作。
镇元子的声音清冷凛冽。他说,若无脑人,这世界本应是骨人的天下。
骨人坚若磐石,寿命极长,本是这世间最好的统治者。但骨人有一个致命缺点,无法从天地间获取营养和氧气。于是骨人藏于脑人,充其骨骼,共生为人,便如藏身于璅蛣中的腹蟹,取其之食。等璅蛣身死,再换下一只璅蛣便是。但脑人不愿为他人做嫁衣,在长久的自然演化下练得了剥夺骨人神识的本事。从此世上再无脑人和骨人,只有人类和尸骸。
“这人参果……”我隐隐有些猜到了。
“没错,这人参果便是脑人,我族造出的脑人。
“脑人不过是我们的衣物,而这世界终有一日将归属我族。白骨,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5
镇元子并未勉强我当场表态,只让我拿着人参果把玩几日再做决定。
明月带我回房歇息。路上,我又陆续见到了一些别的骨人,又或是骨猴骨鹤。明月说,骨人本就随脑人的形态而变,若投入飞禽走兽胎中,自会长出飞禽走兽的骨骼,无甚稀奇。但多数时候,观中走动的还是人形骨人,他们身着葛巾布褐,应付着善男信女,观中香火很是旺盛。
焚香丛丛,明灭有序,就像上元灯会那夜的火树银花。
上元节,是我身为顾瑶的最后一日。
千门开锁万灯明。每到上元节,武威城的街巷里便穿梭着数不胜数的灯狮灯龙,花灯挂在家家户户门前,将这西凉小城都捂热了。我阿娘是一名灯匠,扎了一辈子灯笼。阿娘常说,人就和灯笼一样。人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灯面上活灵活现的画,但真正决定这花灯能用多长时日的,还得是那看不见的灯骨。
什么样的灯骨才算好灯骨呢?我问阿娘。
阿娘笑笑,说以后我便懂了。
后来我遇见了谢长安。
我那时想,谢长安便是这样一等一的好灯笼了。他是镇国护民的游击将军,守着一方平安,不可能没有高风劲节的风骨。
于是在新婚当日,谢长安遵循习俗询问我要将字样镌刻于何处时,我径直拍了拍脊柱,道:“这里。”
“会很痛。”谢长安蹙眉道。
我无知而坚定地点头,“就这里。”
于是一整月没能下得了床。
那时我还宽慰自己,那些将字样刻在手腕、指节又或是踝骨的将士家眷,若真被突厥人捉住了,不仅少不了断指断手,更难被亲人辨出埋骨故里。
而我就不一样了。那些粗蛮的突厥秃驴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会将印记刻在脊柱上。而若是连这个印记都被他们发现了,想必那时我也活不了了。
谁知我死后竟是这么一出。
忆及此,脊柱又开始隐隐作痛,我对着铜镜一看,才发现新婚当夜谢长安刻下的“谢氏夫人”字样竟还保留在骨面上,难怪初遇时明月那么惊讶。我看着脊柱处刻着的“谢氏夫人”字样,更加放心不下谢府。
于是我悄悄裹上人参果,穿上厚实的斗篷、面巾和鞋袜,连夜赶回了武威城。
皇帝取消了上元节期间的宵禁,武威城高悬着赤红花灯,亮得和白昼一样。谢府也不例外,张灯结彩,时不时还能听到祝酒声。我摸索至中堂,被吓了一跳。
谢长安穿着常服,正与两个做突厥打扮的人觥筹交错,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好不惬意。
我有些慌。谢长安没有发现我失踪了吗?
我屏息藏在中堂旁的花丛中,侧耳聆听,却越听越心凉。
我的夫君,叛变了。
无非是那些戏本子里的烂俗桥段,军队被俘,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一眼看中了谢长安,愿招他做驸马。谢长安答应了,于是整支军队都没了性命。
“谢兄,听闻府上家眷……”不知为何,这突厥人的声音竟莫名耳熟。
谢长安将手中的杯酒一饮而尽,“区区贱婢,不足挂齿。”
我的心堕入冰窖了。
“如此便最好。”突厥人松了口气,又将酒与谢长安满上,“实不相瞒,舍妹对那位好奇得紧,几日前便请去做客。”
谢长安脸上笑容不减,“如何?”
“那奴中途跳了车,追上去时已断了气。”突厥人道。
夜风料峭,像刀子在空荡的头骨内翻滚。我想起来了,这突厥人便是将我丢至乱葬岗的二人之一!是他们破门而入,一剑要了我的性命!
谢长安缓缓放下酒杯,烛火噼啪轻响,正当我以为他会发怒时,那浮夸的笑容已再次出现在他脸上,“婢女惊扰了公主,以死谢罪,死得其所。”
我只觉怒火嗡一下冲至颅顶,再忍不住,一把推开中堂的门,咬牙切齿道:“谢长安!”
谢长安的声音断了。
“……夫人?”突厥人瞪圆双眼,尖叫道:“鬼!鬼!鬼啊!”
谢长安没有犹豫,径直从墙上取了弓,挽弓射箭。
箭势破风,穿透那层薄薄的人参果皮,射入了我的脊柱,正中“谢氏夫人”四字。
我这一生只见过谢长安两次挽箭。一次是初见,他射下我头顶的蝴蝶花灯赠予我,一次是现在,他要一箭取了我的性命。
骨人质坚,这一箭并不很痛。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再也回不去了。
那盏名为谢长安的花灯,被自己的箭撕开了灯布,一箭射中花灯正中的灯芯。
烛光噗嗤一声,就灭了。
谢府突然变得灯火通明,铺天盖地的脚步声朝我逼近。一个瘦削的身影出现在我身侧,拉着我朝门外冲去。
是唐三藏身边尖嘴猴腮的大徒弟。
6
那唤作悟空的大徒弟身手灵敏,带着我东跑西窜,最后闪进了一处别院,谢府的奴役举着火把从墙外跑过。
夜凉如水,我麻木地看着眼前一行人。唐三藏,三个嘴脸凶顽的徒弟,还有一匹白马。
唐三藏握着串珠,喃喃念着阿弥陀佛,朝我行了一礼。
我不理他,自顾自地在角落坐下了。
悟空举起棍棒便要打,“你这是什么态度!”
唐三藏摆摆手,再次制止了他。
后续几日,我便待在他们临时落脚的这处别院。唐三藏师徒忙着为城中百姓义诊,我落了个清净,得空想明白了很多事。
小道士明月说的没错,我是货真价实的骨人。
我有坚如磐石的骨骼,所以谢长安的一箭除了在我脊柱上戳了个不大不小的窟窿外,其实无关痛痒。我不是谢长安的妻,所以当我发现谢长安的背叛后,愤怒远大于悲伤。我没有肌肉,不能像脑人一样喜怒哀乐形于言色,所以无论我是想哭顾瑶的不值还是想笑她的荒唐,我都做不出任何表情。
但有一事,我却始终想不明白。
月华昭昭,我敲响了唐三藏的门。
“明月说,你体内的骨人已跟随你族十代族人?”
“正是。”
“可是镇元子说,脑人是骨人的宿敌……”我拧巴地问道:“为何它愿跟随你族这么多年呢?”
“夫人,”唐三藏打断了我,“你觉得,人为何物?”
我思索片刻,“我曾以为,人便是人,独立而生,与这世界相识相知,再空空而去。”
唐三藏笑道,“此言不假,却漏了一处。”
我一脸疑惑,他便继续道:“世人只道人是万物之灵,却不知,这万物之灵,本就由万物组成。于外,人于农田处讨五谷,于走兽处寻布匹,于天地间求晴雨。此为外共生。于内,人有骨骼筋膜、经络血脉、五脏六腑,各司其职,此为内共生。
“今日是这骨人有了神识,便觉得自己吃了亏。那若一日五脏六腑也有了神识,又当如何?”
我被唐三藏讲晕了头,“可我身为骨人,不当与骨人结为一派吗?”
唐三藏笑了,只见他肌理逐渐透明,体表泛出乳白色的光晕,隐隐透出了他的头骨。
那头骨一张一合,声音隔着脑人穿透了出来,“夫人,你当了两年谢将军的夫人,便要一生一世地当下去吗?”
“身份,不过是你为自己拷上的枷锁罢了。”
7
结束和唐三藏的对话,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悟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听懂。佛家人说话总是这样云里雾里。
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停滞下去,因为我的人参果快枯萎了。
或许是因为谢长安那一箭打破了整个人参果的循环,那处硕大的箭伤在经历流血发脓后,一点点变黑,而这带给我最直观的体验便是,每日运到我骨骼内的能量一点点变少了。
我腆着脸去五庄观找明月。
明月看了我许久,叹了口气,带我去了五庄观山下的一处岩穴。
岩穴极深,越往内走,顶上的空间越大,最后形成了一块天然的广阔地段,人参果树的根穿透穴顶,和钟乳石纠缠在一起。沿墙密密麻麻铺着陶瓮。陶瓮里装着酒精,腌泡菜似的放着各式器官。正中是几张石案,各放置着一具尸体,几个骷髅骨人拿着金击子围站在旁,小心翼翼地割开尸体表皮,摊开,将已死去的骨人和经脉分离。
明月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人参果皮,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这才带着我从这些石案旁一一走过。
一个被烧成炭的小骨人。“偷溜回家,被阿娘当鬼怪烧死了。”
一个趴在尸体上痛哭的骨人。“儿子苏醒时被脑人杀死了。”
一对双手紧握、骨头散成碎片的骨人情侣。“被人识破了身份,乱棍打死了。”
复杂古怪的情绪在我心里滋生。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盏花灯,被这情绪一吹,噼啪掉出了一朵火花。火花在灯内飘啊飘,落到了花灯外的衬布上。熊熊火焰包裹着花灯,一炷香后,整盏花灯只剩一具烧至漆黑的骨架。
唐三藏说,身份是我为自己拷上的枷锁。
我将目光投至离我最近的那张石案。这是自我进来后他们处理的第三具尸体,前两具都因操作不当而中道崩殂。这一具眼看就要进入收尾环节,却在拆卸头骨时,不知触到了哪里,溅起一柱血花。
血花喷洒在石案旁每个骨人身上,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骨人没有肌肉,生硬的骨头很难直接传达出情绪,但这仿若时间静止的一刻,我却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悲伤。又一台分离手术失败了。
“戏本子里说,人参果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熟。”明月轻声道,“仔细想想,骨人一族确实也摸索了上千年。”
“一开始,没有骨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们以为自己是妖怪,是鬼魂,是这个世界上本不该存在的生物。直到一位医者变成了骨人,才探明了我们的身份。他发现骨骼内自有一套循环机制,使得骨骼相比肉体而言可以千年不腐,于是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我们不是怪物,而是一个新的物种,一个和脑人共生了千年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物种。他为我们起名为骨人。后来,更多的骨人被他找到,更多的医者成为了骨人。他们教导我们如何剖开皮肤肌肉,结扎血管处理韧带,用竹筳探明血脉,用金击子缝合经脉避免感染,用冰石作解剖台延长时间,用烈酒浸泡器官留作研习。那时,战场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数不清的尸首,数不清的案例,以及挣脱束缚的新生同胞。”
“可即便如此,努力了上千年,我们如今的技艺亦不过才能从百余具尸首中解构出一副皮囊。而一副皮囊最多不过使用十年。”明月恨道,“这一切,皆因脑人而起。”
他看向我,“白骨,天下没有白拿的人参果。你做好决定了吗?”
8
骨人的寿命极长。但这个决定我却做得很快。
阿娘常说,人就和灯笼一样。人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灯面上活灵活现的画,但真正决定这花灯能用多长时日的,还得是那看不见的灯骨。
什么样的灯骨才算好灯骨呢?我问阿娘。
阿娘摸摸我的头,说以后我便懂了。但千万要记住,灯笼灯笼,先有灯,才有笼。无论灯骨灯面怎样千变万化,笼中烛火一熄,灯笼便成了废纸弃木。
我听不懂唐三藏所说的内外共生,只觉得,脑人与骨人便是这灯面灯骨。
骨人的寿命比脑人长千百倍又如何,没有脑人为它传输清泉氧气,排污纳垢,等待骨人的只会是漫长的死亡。脑人的狡黠聪慧胜过骨人千百重又如何,没有骨人为脑人提供支架,脑人也不过是那海中人尽可欺的水母。
骨面相争,终究是两败俱伤。
“然后呢?你怎么选的?哎你快讲啊你!”唐三藏尖嘴猴腮的大徒弟拿着铁棍在我身旁跳脚,震得我这洞穴簌簌落灰。明明已经是从天竺回来的得道高僧了,还是这般猴急,当真死性不改。
我瞪他一眼,“你师父到底是让你来送特产的还是来拆家的?”
他一听到师父耳根子便软了,铁棍也收回了兜里。
我是真没想到,唐三藏师徒能从西天取经归来,更没想到,他们的取经之路还被编成了戏本子,竟然还有我的戏份——虽然离谱得不成样子。
我在捡来的美人榻上翻了个面。没了人参果后,这些日子我是越来越难动弹了。
大徒弟又被我脊柱上的刺字吸引了去。
“你这字刻得倒好,刚好挡住那箭留下的窟窿。”他眼尖得紧,只听他一字一字地将那刺字念了出来,“白……骨……夫……人……”
“你重刻了?”他抠抠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