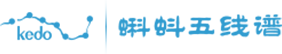疯狂、苦味与蜜糖
本文为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二等奖作品。
2018年“光年奖”评委会评语:
《疯狂、苦味与蜜糖》是一篇有"呼吸感"的小说。悬念精巧,技法成熟,游刃有余地将读者带入叙事节奏中。
——光年奖评委夏笳、迟卉
盛夏小院、此际
我跟你说,刚才你用刀尖挑着半边削了皮的苹果递给我的一刻,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爱情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
我一笑置之。
随即徘徊在我脑里的,是又涩又甜的果汁、远处山峰上的云烟、小院里散发着清新气味的草、这个藤织的吊篮。
还有,倚在我身旁的你,那天生冷傲而又勾魂夺魄的眼睛、节奏稳定地起伏的胸脯。
昨天,看过我收藏的那成千上万的电子杂志,你该记起,以前自己是多么的受欢迎了吧。无数男人甘愿拜倒在你石榴裙下。但我敢保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我对你的感情那么刻骨铭心。他们爱的只是你姣好的面容和身材,而我爱的却是你的一切。
你对这句话有印象了?对,我之前跟你说过。是在两年前罢。
喜来登、两年前
那天,在喜来登,你的躯体也是紧贴着我,皮肤上的潮红正在逐渐散去。当时你很疲倦。你刚挂了经纪人的电话,你已是第二次向他声明对粉丝见面会毫无兴趣,但他仍然坚持己见。你告诉我,有时你也很烦那些疯狂的影迷,但又不得不像投喂宠物狗一样适时给他们点甜头。于是我告诉你,世界上喜欢你的人很多,但爱你的人只有我一个。当年第一次看到你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位天使,立在四周苍郁的山林之间。
你那时正端着印有宾馆标志的杯子,听到这句话,一口酒呛了,全吐在床沿水果碟的刀柄上。你把手臂递起,让我看清楚上面的鸡皮疙瘩。你大笑着说,我的对白就像上世纪就已从电影学院退休的那帮老师写的。不过,你喜欢。
我发现,你的践踏欲又来了。
你冷冷地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不高兴,你把我划到跟你的影迷同一个类别了。你喜欢听他们倾吐崇拜之情,一边嗤笑他们肤浅,一边又乐在其中。
你说,天哪,你闻到了很浓烈的怒气。
我不觉得是怒气,平心而论,更像是嫉妒。
你提醒我,我没有什么可嫉妒的,全世界的男人都只能看着你在杂志封面的照片干舔嘴唇,只有我能把嘴唇贴到你脸颊上。
我不得不再重申一次,爱和情欲是两回事。
你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眼光就像刀一样锋利。你说我是个被俗套死死束缚住的人。你建议我忘掉两件事,第一,忘掉那套可怜的爱情哲学;第二,忘掉你的电话号码。
我靠在床头,呆呆地看着你把衣服穿戴整齐。我承认,这两点做不到,尤其是第二条。
16岁
从16岁那年起,我就没有忘记过你的电话。你那一年生日,本来想让抚养你长大的姑妈给你组织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但她生病了,你很生气,埋怨她病得不是时候。已经在班里夸下海口的你,不得不诈病请假,亲自操刀在家里布置。没人愿意协助你。倒不是大家对逃课没兴趣,只是男生不想被人视作观音兵;而跟你走得近的女伴早知你一忙起来就容易发脾气的性子,个个都找借口推托。只有我,装作不明所以地问你为什么急得团团转,然后半推半就地答应帮你。你掏出一支彩笔,找不到纸,就直接在我手臂上写下你的电话号码。笔尖冷冷的,像你平时跟我说话的样子;又腻腻的,像我平时想起你时的心情。我把那串数字抄在不同的笔记薄和课本里,并分别放在自己房间和学校,即使家里失火,我也不会失去它。很多年过去了,你考去了电影学院,后来大红大紫,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对你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
当然,那8个号码仅仅是在我记忆中颠来颠去,从没爬上电话键。
因为我没有胆量。
为什么?
你大概不记得你生日派对的半年前,有一次,我买了两张电影票,跑去跟你说,我本来约了隔壁班的人,但被放了鸽子,我问你有没有兴趣。你很高兴地答应了。当晚我整夜失眠,第二天戴着黑眼圈回到教室,立马被人推到黑板前。黑板中间贴着两张电影票,一张是我给你的,另一张是已经撕掉副票的前天的票。
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我才知道,高年级的一位男生早就请你看过那出电影了。
当晚,我做了一个古怪的梦,梦到自己是个祭司一样的机器人,而你成了一位女神,你的身影出现在一块块冰冷的石碑上。
或许你会以为,我当时就恨透你了。
没有,而且相反,我对你还多了一层可怜之情。因为你自小父母双亡,姑妈又不怎么管你,使你养成了怪异的性子。
而有时候,怜爱比单纯的爱慕更刻骨铭心。
毕业后
毕业后,我们走上了各自的道路。本来,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从交叉口伸出的轨道一样,永分东西。我也以为对你的感情如同那个虚幻的梦,消散在回忆之中。但50周年校庆那次同学聚会又把我拉回青春期。你出现在宴会厅的那一刻,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切都没有免俗。拥抱、签名、合照,我越来越觉得无聊,也替你觉得无聊。我离开宴会厅,来到花园的无人角落掏出烟盒,构思着提前离开的借口。忽然,花丛响了,你出现了。你化了淡淡的妆,月色之下的你比屏幕上更美,虽然比我记忆中的略逊半分。我很惊讶,你还能脱口喊出我的名字。我感到天色仿佛一下子变亮了,喉头涌起一股咸味。我清了清嗓子才问,你最近怎样了,我指的是,除了娱乐网站上能看到的那些。你笑着说,你也没有比各大媒体更多的私家料了,他们报道的比真实还多了许多。你说话时压低了声音,大概是怕旁人听到。我忽然觉得我们像在共同守一个秘密似的,就像当年到你家筹办生日派对前,我们一起为了请假而跟老师撒谎。尽管心跳不断加速,但我努力把持着情绪,刻意表现得不再是个懵懂的少年。可是,你的一句话,立刻打破了我的努力。你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约过你一次看电影。我怎么可能不记得?你说为了报答当年我的情谊,明天就请我去看电影。
有意思。电影的女主角居然亲自跑到电影院观看。那短短的120分钟,点燃了我追求幸福的愿望。
从我们恢复联系起,我就像被困在一口甜蜜的井中,一如当年。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一个不敢告诉别人的幻想。我不顾一切地要出人头地,至少终有一天挽着你的手出现在记者面前时,他们报道的侧重点不会是我低微的身份。你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家势,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得付出多少,才能在野兽横行的新城金融区迅速站稳。但,当我在金融峰会上作为最年轻的嘉宾上台前,我看到对面马路公交站台上的新电影广告,我明白,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喜来登、两年前
你找到了裙子,却用它捂住眼睛,仰面又倒回宾馆的床上。你嫌我啰嗦那些陈年旧事,很浪费时间。你不傻,我那时的心思,你一直都很清楚;要说唯一不清楚的是,我变成机械躯体后的心思。
你承认,自己一直都不明白,一个机躯人竟会有这么强烈的感情。
“因为这个机械躯体是因你而有的。”我缓缓地说。“正是为了‘配得起你’这种古老而可笑的想法,我逼自己更努力,抓紧每一个机会,甚至包括集资的机会。最后,我终于跟你同一天上了网站首页。可惜,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我还记得那条标题,《惊天非法集资案,令你脑洞大开》。换着上个世纪,我这种罪是要判死刑的。但这个年代,我只需要被洗一次脑。精通意识神经学的法警把我送进手术室。我还记得自己问他,洗脑会不会把所有爱恨情仇都洗掉。他说不会,只有我策划作案时到受刑这段时间的记忆,以及犯罪技能会被删滤干净,以后我一听到‘集资’两个字就会反胃。我又问,洗脑就去洗好了,为什么要把犯人的躯体全换了?他有点不耐烦了,反问机躯处理应用于司法已经三四年了,你上网一搜一大把,怎么还一无所知?脑信息定点删除得搞几个小时,这个过程需要完全断开脑部和躯体的神经连接,你见过有人被砍头半天后,躯体内脏还能正常的吗?受刑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也会在我躯体内植入‘预防犯罪装置’。”
我拉着你的手摸到后背的一个位置,告诉你,如果切开人工皮肤的话,你会看到里头藏着一个重启键,一旦他们发现我再有犯罪倾向,就会把我抓回去,按下这个键。当然,在应急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远程操作。然后,我胸腔内的洗脑装置就会工作,可它没有法警手上的那套精密,它不能定向洗脑,只能让整个大脑遗忘掉最近一年的事情。大概,司法专家觉得犯罪的念头多半是一年内萌生的。
对我的付出,你再次重申,你很感动。
我把碟里的苹果洗干净,用刀削皮分了一半给你。
你不要,说赶时间。房间开到明天中午,我要是累的话,可以休息一下再走。
我告诉你,机躯体不会累,只会厌倦。不过,有一件事我不会厌倦,就是回味你的一切。
你指出,很多人都会这样,回味你的某个镜头、某句对白。
我回味的不是那些虚假的东西,而是我和你之间真实的点点滴滴。从少年时认识你那天开始,到取得你的电话、被你取笑、与你重逢、直到今天。
你高高在上地吻了我一下,说我要是表现得好的话,还有机会跟你再聚一次。
不,每次跟你相聚,都有不同的回忆,我会把录像放出来一分钟一分钟地回看。
你立即放下手袋,问:什么录像?
我坦承,我们每次聚会我都录下来,到现在已经有几十T的文件了。
你看着房间的四周,大叫起来:你居然在宾馆偷装摄像头?
我提醒你,我的机械眼本身就是个摄像头啊。
你急切要知道,文件存放在哪里。
在胸腔的磁盘里。机躯人比普通人方便的,就是不会忘事儿,他们随时可以启动录像程序,让经历的一切录在磁盘中,需要的时候,大脑通过生化接口读回数据,往事就会如在目前。
立即把文件删掉,你喝令我。
我直摇头,这是司法机关的一种设定,一旦录下就无法删除。这样,也方便他们在我再次犯事后获得证据——虽然一般来说,谁也不会那么傻在蓄谋犯罪时启动录像。
你跳起来说,还会有别的人看到我们在一起的事情?
我请你放心,我不会再犯罪;而且,即使犯罪了,我再一次被洗脑时,磁盘中的数据也会被清零,他们不会让犯人的思想再受到作案历史的污染。
你脸色苍白地看着窗帘外,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在埋怨我:一旦有记者知道我和你的关系,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读取你磁盘里的东西,那将会是本世纪娱乐圈最大的丑闻。
我安慰你:他们没有权限,读不出数据的。
你责备我对狗仔们的手段一无所知。
爱情怎么是丑闻?明星不是人吗?我反问。
你大声喝我住嘴,你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要拥抱你,让你冷静,被你一手推开。
你骂我是个伪君子、卑鄙小人。你的前途和命运,全都被我这个弱智的混蛋操控住了。
我摇着头,站到窗边拉开帘子。
你尖声叫我别站在那里,小心被人看到。
我觉得你太敏感了。
我看着窗外无边无际的大海,就像听不到你说话似的。你不知道,我心里也像蔚蓝的海面一样翻着波涛;你不知道,我双手在颤抖;你不知道,我在祈祷一切顺利;你不知道,我在为接下来的事忏悔;你不知道,我在憧憬遥远的将来。
突然,我感到后背一凉。
你动手了。
我从玻璃窗的倒影看到你咬着牙关、用尽全力,把水果刀刺向我背后重启键的位置。
也许在这个动作的几秒钟前,你反复考虑过几种方案。抄起椅子砸向我的头顶?可金属颅骨很硬。把我从高楼踹下?可磁盘数据很难被外力破坏。把我浸在水里?可机躯人的防水是达到深水级的。还是直接向重启键下手更稳妥快捷。只要我的意识被重启到一年前,也就是我们重逢后的第一次单独约会前,那么,你对于我来说,便永远只是一个青涩的回忆。而我和你近来交往的种种记录,也将同时清零。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万万没想到。
刀子刺入我后背,渗出来的是红色的液体。
是血。
你抛下刀,哆嗦着问,怎么会有这么多血?
我忍着痛,苦笑着说,可能刺穿了动脉,或者什么内脏。
你说无法想象,机躯人会有动脉和内脏。
我说,我也是。
你忽然明白了,大声叫起来:原来你不是机躯人!你是人!
我艰难地点点头。
为什么?你沾血的双手插在头发里,喊道,你为什么要装成机躯人?
我叫你猜。
你是这么猜的:我因为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所以干脆冒充机躯人。机躯人和普通人永远都没法正常地在一起,这样,我就不可能有非分之想,而你则可以放心地和我交往。根本来说,这是欺骗!
我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
你拉开门,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居然忘了给我叫急救。
这的确是欺骗,我暗自想,但根本来说,这是爱。
庭审、两年前
你并不意外,法庭外蜂拥而来的传媒比任何一次首映礼还多,随着审讯的进展,关注的人不减反增。
这桩谋杀未遂的案件一开始就失控了。
我们之间交往的大量细节被公诸于众。甚至连我们母校的师生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其中一位不堪其扰的旧同学还被控殴打堵在他家门口的记者。那桩案件的开庭被插在你的两次庭审之间,而且还是在同一个法庭。
你被描绘成一个人前装清纯、人后玩心计、不择手段地上位而又冷酷无情的女人。请别介意我这么说,两年前的你,只怕比网站报道的更可怕。小报上给你冠上的称号五花八门,每个都以一个女字旁的字收尾。
你否认所有罪行,但没人相信你的话。开始时,大概你会觉得,我会设法给你脱罪。你通过各种间接渠道向我暗示这一点。
然而,这么多年来,你第一次没把我控制在股掌之间。
我指控你,为了保护自己清纯玉女的公关形象,多次阴谋除掉我这个地下情人。你的辩护律师很精明,立刻质疑假如我真的早知有危险,为什么不一早离开你。我用一种哀痛的语调答道,我只把那些事情视为意外,直到背后挨了一刀才想明白自己一直都身处危险之中。
辩护律师继续进逼:假如她真的那么看不起你、甚至恨你,为什么又一次次地找你?
我把准备已久的答案抛出来:因为嫌疑人总在人前戴着面具,令她的人性早就扭曲了。她经常对我说,那个圈子就像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谁都不知道下一步踏出去,踩到的是不是地雷。所以,她需要一个人帮她把绷紧的神经逐条舒梳回来;如果这个人是在大众面前隐形的,那就最好了。总而言之,我对她的存在意义,就像一个无可替代的慰安妇。
这个词像深水炸弹一样,把你严密的铁甲炸开个巨大的口子,黑沉沉的海水呼啸而入。你一下子崩溃了,披头散发地向着证人席高声叫骂,你说后悔没有真的早动手把我这个心怀怨恨的混蛋杀掉。你推开辩护律师、用头顶撞法警,还出言威胁法官。
在下一次审讯中,辩护律师花了好大劲想为你的失态圆场。但你又一次陷入歇斯底里。因为你见识到了我几个月来精心策划的成果,每一条证据都经过我事先反复推敲,足以让最仁慈的法官,坚信只有洗掉你大脑的某些部分,才能让你的心灵变得像外貌那么美好。
盛夏小院、此际
不,别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
别激动,也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
先把刀给我,好。
我承认,是我一步步把你导入预设的轨道中。但你不觉得,这样才是你最合适的人生吗?你不用再藏在那厚厚的面具下做人,不用受困于那近乎疯狂的控制和践踏的欲望。
没错,你骂得对,这里头也有我自私的成分。当你变成机躯人之后,你那股咄咄逼人的傲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能理解你的苦楚,人们面对机躯人,就像18世纪的美国人看到黑人一样。尽管不断有团体呼吁消除对机躯人的歧视,但这些宣传本身又加深了公众与机躯人的隔阂。而法警把你犯案前一年的记忆全部洗掉,又恰好把你对我最颐指气使的那一段历史抹得干干净净。于是,一年前,当我再次出现在你跟前,你才会那么容易接受我。
然后,你继续走在我预设的轨道中——哦,不,是我们。我们手挽手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山林里,享受着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苍翠的视野。我如今在金融界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你几辈子也不用愁柴米油盐的事,因为非法集资罪取消了。
我也给你削个苹果吧,嗯,这刀,你认得不?
就是你刺向我后背的那把。
为什么没在司法机关的证物档案里?
因为我给换了一把。
来,瞧清楚些,这是一把伸缩刀,刺入皮肤几厘米后,在碰到内脏之前,刀尖就已经定住了。法医给我检查时还连声说我走运。其实,静脉是被你刺伤了,血也流了不少,说危险么,也有点,可是不大可能伤及性命。你离开房间后,我立刻就把伸缩刀换成有你以前指纹的水果刀。虽然二者的纹饰外观都有点出入,但我料定在法庭上,你绝不可能、也没心思辨认出来。本来,这种伤势不算致命的伤人罪,可以轻判,但你在向法官咆哮时,就已经放弃了这个机会。
这些事,在我心里积了一阵子,又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大半年前,第一次出现这种状态时,我几乎要找个神甫、或者心理医生来哭诉了。后来我想到,何必这么傻,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好的诉说对象么?你不记得,很正常;这事,其实我已经跟你倾吐过好几次了。
啊,回来我身边吧,我只是想拥抱你,度过接下来的这一分钟。我想在这宁静的山间,看着天使般的你,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样子,那多么像一幅文艺复兴的油画。
你去哪里?要找电话?告发我?
何必多此一举呢?
在山间生活的这一年来,难道不是你一生中最快乐,最安稳的时光吗?
好了,坐下来,深呼吸,听我说一句话,就一句:你的机躯胸膛里有个磁盘记录着你的所见所闻,你知道的吧?
你知道,好。你也该明白,这事我也知道。
不用护着你的后背。即使你已经启动了录像,也无济于事。
我两年前接的一个风险投资项目就是做远程机躯控制的,你认为,我还需要用外力强行按下那个重启键么?
看到我手机屏幕没有?还剩下20秒。是你重启程序的倒数。
所以我建议你就坐在椅子上别动,免得脑部被冲击时,身体摔到在水泥地板上。
放心,我会呵护你的。
再一次醒来的时候,等待你的依旧是苍翠的山峰、幽静的别墅、世外桃源的生活,和永远爱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