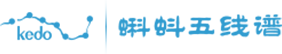明暗之间
编者按:
本文为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作品。
2018年“光年奖”评委会评语:笔触细腻,故事完成度较高,伏笔自然。
——光年奖评委夏笳、迟卉
一
隐隐一声雷动,把我从纷繁的思绪中拉扯出来。
抬头一看,天空中,云团又翻滚起来了。像是铺开的墨晕一样,色深的地方说不上是黑色蓝色,色浅处也说不清是灰色白色,唯一能确定的是,顶多还有五分钟,又一场雨就会下下来。
地上还积着上场雨的水,柏油路的街面一片小海洋,路标线反射着暗黄色的光,从水底透上来,有几分人工智能大觉醒以前的古旧时代的味道。不知道是下水道清理系统又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机器人们觉得让人类湿湿脚也有趣,所以故意不来清理。
撒豆子般的声音倏地响起,夏天的大雨说来就来。我赶紧后退两步,站到医院大门的屋檐下面躲避。瞧瞧手表,又转头看看门诊大厅,盘算着还有多长时间容我赶到办公室。
在这个物质达到极大丰富的年代,依靠福利机构的基本保障,本来已经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有人选择工作,不是为了精神的满足,就是要支付一份额外开销。我属于哪种呢?或许也有精神的追求,但缺钱是肯定的。
身怀哲学和数学双博士学位,我找了两份工作,上午市三中教初中生数学,下午社科院地方调研室做研究。今天周六,学校是不用去,可调研办公室有个加班却躲不了。
雨下大了,砰砰砰砰的,好像要把玻璃顶篷打穿。风卷进来几粒雨点,砸在我额头上,霎时炸成一片水花,拿手抹去,立刻又是几颗打上来,我只好再后退两步。不经意地一瞥,只见旁边一个姑娘同样被雨赶着退了进来。
见她也注意到了我,我赶忙点点头,示意问候,她也紧张地躬身回应,目光望向地面躲避我,白净的脸庞带着几分羞涩。似乎我们的行为都让彼此有点惊讶了,于是我们各自转开头等起了自己要等的人。
清儿还没有出来,我再看手表时,又是十分钟过去。已经快要十二点四十,两点半我就得到办公室,这一路过去可不近,最多还有十分钟给我等她。
我叹了口气,脑袋里开始胡思乱想。但是有些事不想则已,一想起来就是千头万绪,叫人痛苦,我只好狠狠甩了甩头,逼自己暂时放下。我好像真的老了,区区头痛也难以忍受了。想到身边有个年轻姑娘,我决定看一看她,来转移思绪。
大雨正酣,我装作打量四面环境,眼光朝姑娘那边探了探。她专心等待之余,又好像在想着什么,时而修眉微蹙,时而长吁一口气、动作轻柔地左右远望。那个幸运的人迟迟不来,姑娘一头长发随着窈窕清瘦的身子晃动,五十公分的黑色短裙是那么引人注目,纱衣染了雨水,稍稍地贴向肩背,露出她青春躯干的线条……
我知道这样看一个女孩子不礼貌,但是她不知道我在看她,就算不伤害她了吧?这行为在不伤害她的同时满足了我,不算是一个良好的决策吗?不不……
“哥,你怎么不往里走点啊。”
我脑海里正要为我的偷窥辩护,清儿已经出来,走到了我身边来。她伸手在我身上抓,看我淋湿没有。
我把她的手拿下来,说没有关系,一边打量她。
清儿个子要有我高了,十七岁,本该是她一生中最为青春闪亮的时候啊!可她却脸上带着面纱,只露出双老鼠般的小眼睛,看得我心中不住刺痛。
她歪过头,目光越过我,落在旁边那避雨的姑娘身上:“姐姐,你要去哪儿啊,我们送你去吧?”
“哦,不用了,非常感谢。”姑娘一怔,随即微笑着对我们的友好致谢。
她也趁机得以仔细观察我妹妹。她应该早想看了吧?——清儿长裙拖地,长袖衣服遮身,头上面纱头巾包裹严实,大夏天里,这样的装束,实在不能说不怪异。
其实唯一露在外面的眼睛更招人注目,异常地小,眼角的轮廓也变了形,看一眼就足以让人心生厌恶……我下意识地把清儿挡到了身后。
“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谢谢你们。”姑娘再次向我们鞠躬,摆手示意告别。
我挤出个笑给她,转过头启动了手表上的呼叫程序。
飞梭从雨幕中破空而来,在医院广场上减缓了速度,然后降低到离地约三十公分的高度,划着水痕飞过来悬停在医院门口。
前车门打开,我的人工智能管家老猛撑着伞走了过来,他像模像样地嘟囔道:“你们人类真是麻烦,淋点雨又不会短路,干嘛每次都非要我打伞来接。”
我回呛道:“理论上你们铁皮人要真正懂人类情感,至少还得五十年呢,骄傲个什么劲儿!”
老猛撑着伞,我抱起清儿上了车。
清儿的身体愈发差了,抱起她时,我悄悄捏了捏她小腿,她没有反应,肌肉僵硬得像是超市里的冻货。背部的畸骨也好像变尖了,经她一米七的个头一压,刺得我胸膛发痛。我的心更痛,一时竟不知道是该悲伤她的身体状况,还是该庆幸她还在我怀里了。
飞梭离地而起,上升到C类飞行器允许的七米到十四米高度,老猛在前排驾驶,铁皮脑袋里发出猥琐的笑声:“我看那位小姐很漂亮啊,肤白貌美,三维标准,你没有考虑追求一下她?”
“是挺美的,可惜人家有男朋友了呢。”清儿说。
我心情烦躁,忍不住怒骂道:“你他妈的铁皮脑袋能不能别整天不干人事儿?非要我把摄像头给你拆了才爽是吧!”
老猛“哦”了一声,低落地闭上了嘴。
清儿摸着他的铁头安慰他,一边为他辩护道:“哥你别这么说嘛,其实老猛说得也不错,你都三十四了,我都要成年了,你这么老是单着也不行啊。我有病你又没病……”
“你如果能安心接受手术,把身体治好,我还会有这些问题吗?……”我话没说完,忽然听到一声低低的啜泣,清儿花生米大小的眼睛里淌出泪水,打湿了面巾。
我忙改口道:“当然了,你接受不了那个,我也是理解的……其实我单着也不怪你,主要是没遇着合适的嘛,我喜欢的姑娘又看不上我,没办法啊……你放心,我会努力找的……”
我语无伦次的安慰没什么用,说出去的话收不回,必然又深深刺痛她了。她会以为自己耽搁了我而陷入自责,又跨不过心头那道阻碍,最终在“伤害哥哥”和“伤害别人”的矛盾中不断折磨自己……
我这个该死的人啊!
我只能把她搂过来,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哄孩子一样,听她的啜泣声慢慢变小。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老猛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哦”了一声,又不敢多说话,默默按下了烘干按钮。脚下传来轻微的响动,温暖的风斜吹过我们后背和脚踝,烘干着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和鞋子。
“总算办了件人事儿。”我夸奖说。
“嘿嘿,为您服务,鞠躬尽瘁。”老猛发出谄媚的笑声,不失时机地解释道,“其实咱啊,就是说话冒失了些,正在努力学习改进中。可咱对您的爱情的关心是真切而忠实的,这一点可不比清儿少……”
老猛的絮絮叨叨把清儿也逗笑了,他们慢慢又聊了起来,我在“爱”来“爱”去的一堆词汇中忽然灵光一炸,回头向远郊医院看去,可那避雨的地方早已消失在天际线尽头了。
二
7月过半,梅雨季节悄然结束。太阳已经连着把大地烘烤了一个周,办公室外面的树都蔫嗒嗒的没了力气。按照本地的气候规律,接下来两三个月,炎热的日子还将占大多数,直到秋冬季节来临。
我走出办公室,心力交瘁。看着血色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沉默无边的黑暗一点点从地底下升了上来。同事们三三两两从楼里走出,我一个人,多少还是有些孤独。
主任老邓最后出来,他拍了拍我肩膀,问我是不是没带车,是否需要送我一程。我说不用,我想自己走走路。他安慰几句,没有再多劝,随后飞梭腾空而起,尾部喷着淡蓝色的荧光远去了。
我又呆了一会儿,待天色完全黯淡下来,转身向北边走去。
这个星球上的城市早已失去了拥有夜晚的权利,通明的霓虹灯蛮横地照亮着每一个角落,无论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我常常反思人类的这一做法,更倾向于批判。谁赋予了人类永久照亮地球的权利?我想那些愚蠢的大多数按下开关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有的人还有颗欣赏黑夜的心。
大大小小的飞梭在头顶川流不息,运货的,载人的,私家的,公家的,各自占领者不同的高度和轨道,地面上少有人走。社会高度发达让聪明勤奋的人有了空前的机遇,但也同样造就了更多懒在家里的闲汉,所以街上常常空空的。
不多时,我来到一栋摩天大楼前。这栋大楼玻璃外墙呈黯淡的蓝色,足有八十五层,轮高度在我们城市排名第一。楼层外表光滑,封闭严实,不像居民楼那样家家有个阳台供自家飞梭泊入。它是这个城市的先进医疗研究中心。
我缓步踱入,大厅里只有一个老王值班,我跟他打了声招呼。在这样发达的时代,老王选择门卫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份情结。情结这东西,在自己身上就天经地义,在别人身上却是那么难以理解,这点我很明白,又很不明白。
人工智能瞬间扫描了全楼的状况,确定短时间内再无别人有使用电梯的需求,遂将我的身体加以固定,只用了分半钟便将我送到75楼。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我同意之后进行的,虽然人工智能大觉醒后,电脑能初步处理人类意愿,但与此同时,人权至上主义也空前严肃。
75层没有护士值班,只有两位女医生,穿着白大褂,坐在护士站处理科研数据,我与她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短暂交谈几句之后,我来到7509号房间门前,摄像头采集了我的面部信息,房门悄然划开。我走进屋子,墙边亮着淡蓝色的光,隐约照亮着屋内的情况。我没有打开大灯,对接下来要看到的那一幕,灯光黯淡些或许更适合。
屋里空气比较干燥,吸第一口差点呛到我,不过反正也没什么活人在这里长住,这样的干湿度还是比较合适的,至少可以减少微生物滋生。四周弥散着淡淡的麦香味,其实是消毒剂的味道。
我走向蓝光闪烁的隔离室,透过厚厚的玻璃层,看望安睡其中的美丽女孩。她穿着宽松的睡衣,长发铺在背后,鹅蛋脸白净又匀称,睫毛浓密而修长。
这双眼睛睁开后,会有多么明亮动人呢?不,甚至都不需要睁开。她就这么安静地睡着,便让人无比怜爱了。要是清儿是健康地长大,这时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吧……
我情不自禁伸出去的手,被玻璃所阻隔,这把我从幻梦中拉回现实来。屋里忽然间变得让人无比压抑,我起身走到窗边去,窗玻璃自动开出一个口子,我把半个身子探出去,点燃了一支烟。
我以前并不抽烟,是几天前才开始的。几天前看一本百多年前的小说,封面上那个胖作家抽烟的神情吸引了我。他叫路遥,名字又短又长。他抽起烟的时候,神情困顿而满足,痛苦而坚韧,那正是我所需要的力量。
烟雾缭绕中,我看着城市里永恒的光。近地处的飞梭、远处的飞机和更远处的飞船占满了天空,我想那些在书上读到过的所谓“星光”,此生恐怕都难在地球上看到。
这些人造的光明和温暖,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如果是坏,难道要再让贫瘠地区的人民回到过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才好?可要说好,又叫我如何能承认——
十五年前,可控核聚变经历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失败,辐射泄露,夺走了我双亲的生命,不到两岁的妹妹清儿也因为遭受核污染开始全身畸变……从那以后,能源危机彻底解决,世界亮起来了,我的人生却永坠黑暗之渊。
三
11月,又一个加班日。
晚上十点多,老猛才载着我降落在自家阳台上,车门刚开,一股寒风就迎面扑来,冷得我直打哆嗦,赶紧钻进屋子里。
换了鞋子,挂好衣服,洗过手,看到桌上摆好的饭菜。保温系统正运行着,不时发出滴滴的提示音。
我放轻脚步,走到清儿屋外,想要推开门进去看看她,不料这天她却上了锁。
“哥,你回来了?”她还没睡着。
“是呀,还没睡着么?”我说。
“我……我睡了,饭菜给你热着呢,你早点吃完睡觉哦,晚安。”
我不禁一愣,这很反常!
清儿怕孤独,以前无论是加班,还是因为想去先进中心而谎称加班,我都提前告诉她,她做好一桌饭菜,总要等我回来才肯睡,偶尔实在累了先睡,也从不会锁上房门,要等我回来给她说晚安……
我知道,有些事情在发生了!
我随口扒了几口饭菜,回到屋里打开电脑,登录到先进医疗研究中心的网站。点开监控页,左边旋转着一个三维建模的人体图像,右边是相关的一些波形图。信息显示,“三妹”很健康,各项指标正常,年龄达到16.4周岁。她在培育室里的发育速度是正常人的八倍,在两个月后将达到17.7周岁……
我的心抑制不住狂跳起来。但想到一切还没有结束,一切也可以说还没开始,能不能走好最好一步,我实在难以把握。
我思量着,不能被动等待,每个计划总有失败的可能,我得做好多手准备。
清儿粘我少了,抱着手机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常常是坐在我身边,忽然地就爆发出一阵娇笑,我侧头去看她,她小小的老鼠般的眼睛面对着我,露出不自知的羞涩与躲闪。
我微微一笑,往她脑门儿上敲敲,喝口茶,又继续在可能世界里演绎着所有可能的情况。
我依旧有时加班,有时谎称加班,捱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时,她总是房门紧锁,有时装作睡着了,故意不回答我,却不知道即使隔着门我也能听出她呼吸频率的差异。
12月24日,我对清儿说要通宵加班,让她若是害怕,就去小刘姐姐家借宿一晚。小刘姐姐是清儿在远郊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我们兄妹俩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清儿满口答应。
次日早晨,我早早从先进医疗中心75层出来,走到公司楼下,等待老猛开着飞梭来把我接回了家。清儿不在,打电话问小刘医生,也没在她那儿。这时候我心里不能说不担心。
老猛询问要不要报警,我说先不麻烦警察,自己找找再说。
我发动所有认识的人帮忙,终于在傍晚时分找到了她。她趴在城南一家酒吧门外的露天桌上,睡着了。
萧条冬日的树干下,落叶满地,酒瓶子堆了一桌,满身包裹严实的清儿趴在那里,不像一个人,像是一堆凌乱的衣衫。
我让朋友们保持距离,独自一人走上前去。抬起清儿的脸观察,她变形的五官之间满是泪痕,这一夜一天,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心头绞痛,但也知道,关键的时刻来临了!我替她拉上面纱,给她披上了我的衣服。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看眼前是我,再看周围的环境,瞬间清醒过来。慌忙伸手摸脸,摸到脸上的面纱,反复确认后,恍惚的小眼睛才流出浓浓的悲伤来。
“哥……”她一头扎在我怀里,撕心裂肺地哭了出来。
我轻轻地拍打着她瘦弱的肩膀,如同无数个惹她哭泣的往常一样。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清儿恍如丢了魂,整日没完没了地发呆。我跟她说我向两个单位都告了假,会一直陪着她,其实已经辞掉了工作。
她要喝酒,我一点不加阻拦,陪她喝,所以整整一星期下来,无论白天黑夜,她都在半醉之中度过。我问她到底怎么了,她分好几次,间断地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两个多月前,一个叫阿勇的男孩突然闯进了她的生活。阿勇也才十七岁,还在挪威留学,笑起来像阳光一样灿烂。他们在一个RPG游戏论坛里结识,阿勇被清儿的谈吐和思想所吸引,在网上聊了几天后,竟然提出要跟她交往的要求。
清儿沉默了一会儿,坦然地告诉对方,自己小时候被核辐射污染,身体发育得比地球上最丑的动物还要丑十倍……阿勇说,这不成问题,他可以帮助她进行躯体转移手术。
这手术我再了解不过了——通过培养疾病患者的细胞,诱导分化出健康的人类躯体,但不产生意识,待新躯体快速发育到匹配年龄后,将患者的大脑连同神经系统整个移植进去,患者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掌握崭新的躯体,则旧躯体上的一切病变自然不复存在。
只可惜,对天生善良的清儿来说,这项技术却是她决不能接受的禁忌之术。
“培养一具完整的身体,却不给她意识,这不等同于谋杀吗?”她问我。
“这怎么能是谋杀呢?现代社会已经完全承认了它……这是一项伟大的医疗技术!新躯体的意识根本就没存在过,没诞生过的生命何谈谋杀?最多也就是流产……”我说。
“难道流产就不是谋杀了?”清儿蜷缩在床上,抱着双膝说,“哥,别为我费心了,就让我平静地死去吧……这些年拖累你够多了。”
人权至上的年代,清儿需要十五岁成年后亲自确认,才可进行躯体转移这种大手术,因为这种手术可能给患者心理带来终生的巨大影响。而她,选择了拒绝。
清儿拒绝手术那天说出的话,让我体验到一种无力挣脱的难受。虽然从懂事开始她就一直说不能接受这个手术,我却万万没料到她如此坚决,任我哀求也好,讲道理也好她就是不接受。
诱导躯体在培育箱里的发育速度是普通人的八倍,她一直拒绝手术,躯体很快就在年龄上远超过了她,算准时间诞生的“二妹”不得不报废,我还没敢告诉她。
这一次面对青春少年的爱情诱惑,清儿还是没有动摇内心,她回应道,自己接受不了躯体移植手术的伦理基础,请求阿勇收回他的错爱。
然而阿勇的顽固也超出了清儿的想象。他甚至没有沉默犹豫,便坚持表示,这年代许多事情都有相应的机器人可以帮忙,正是前所未有的好时候,即使身体不便,他至少要跟清儿谈一场精神的恋爱,圣洁的柏拉图式的恋爱!
清儿终于被打动,在幸福的泪水中答应了他。他们一天天聊着说不完的话题,阿勇给她看北欧的风光和民俗,看极光下的动物和花草,加之都瞒着家长,日子里充满了甜蜜和刺激混调的幸福。
时间过得飞快,阿勇说他圣诞回国,约清儿平安夜见面,正巧这天我值班不回家,清儿便收拾了一番,只身赴约。
“他说他想吻我,可是一解开面纱……他吐了……当着我的面他……”
“谁不想漂漂亮亮的呢?哥你知道吗,即使是我,也好想好想……做个美丽的女孩儿啊……”
在清儿梦呓般的倾诉中,我的神思飘回了她小的时候。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个从小在梦里吵着要做公主的可怜孩子,我当然知道你多么渴望美丽,可上天却连健康都没舍得给你。
阿勇高估了自己的接受能力,他终究没做成柏拉图式的圣人,甚至在落荒而逃时本性暴露地喊了一句“我操”……
这日夜不分的一周里,小刘医生来过几次,我没让她见到清儿。我很感谢她为清儿所做的一切,但一切都结束了,我从远郊医院为清儿办理了退院手续。
一周后,元旦到了,凌晨四点,街上电子爆竹声噼噼啪啪地响,我抬眼看向窗外,全息烟花以假乱真,绚烂得如同要诞生一个新世界的宇宙大爆炸。
新一年的到来让我心跳加速,手也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清儿从宿醉中睁眼醒来,我用熬哑的声音对她说:“宝宝,咱们去做那个手术好吗?就算不为了美貌,你的生命也已经很危险了。没有你,哥哥可怎么活啊?”
清儿失神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我握着她消瘦的小肩膀,直视她的双眼,眼泪涌了出来。
沉吟良久,她终于伸出变了形的小手,搭到我脸上:“哥,我答应你。”
我不禁双手发抖,但及时控制住了。
一个人沉浸在悲伤和恍惚中的时候,许多意识都会变得模糊,包括道德意识,或者不如说,世界观。
“信息确认完毕,手术预约成功!”人工智能确定是她本人同意,手术眨眼间便预约成功。
天亮了,我安抚清儿睡下,然后出去拿了最烈的伏特加,推开窗户对着寒风狠狠地灌下了一大口。
四
“三妹”冲我微笑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好像骤停了一下。
其实这张脸,几年前看“二妹”时就已习惯了,可当她会笑,会皱眉头,会嘟嘴,带上了表情,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时,我心里那份感觉真是很难说清到底是个什么样。
这场躯体转移手术历经53个小时,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换了3班医生才完成,花光了我所有积蓄,还让我不得不向社会福利保障机构申请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医疗贷款,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事。
比起容貌的天壤之别,清儿的声音倒是没多大变化,她有些费力地笑着跟我说:“哥,突然变美了,感觉好不习惯呐,我怎么觉得,变这么美有点过分呢?”
我在她身边坐下,把她的手轻轻握着:“傻孩子,这就是用你的脐带血分化来的,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啊。”
虽然笑得苍白,但看见她在努力笑,我心里就轻松了许多。一切都会过去的,就算她将来再陷入所谓谋杀的负罪感中,毕竟也木已成舟,我相信我可以用赎罪好过自弃之类的道理让她好好活下去。
走出先进医疗中心,白雪已覆满了大地,傍晚的城市华灯初上,照亮着洁白的大地,也在一些角落里投下异常漆黑的影子。
我掏出手机给神秘人Y发了条消息:“多谢帮忙,虽然最后采取备用方案,曲折了些,但我很满意。东西明天快递过来,不留备份。”
“你就不怕有天我再找上你妹妹,告诉她是你让我骗她的?”Y很清楚我不想让清儿知道真相。
“你可以试试啊。”我不怕他威胁,但也不介意费些口舌让他好受些,“你拯救你姐姐,我拯救我妹妹,没有什么交易比这更公平正义了。”
“我姐再怎么样,没有影响到你,你却用她要挟我,这就是你的公平正义?”他犹有不甘。
我不禁叹了口气,这半年来发生的事情在我心头一幕幕滑过。
我决心用爱情来骗清儿接受手术,那是亘古以来威力最大的东西,有很大机会成功。
可茫茫大街上,连人都难得见到一个,谁能帮我做这麻烦事呢?这时候,老猛那对乐于乱拍乱摄的“眼睛”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却是在我意料之外。
很难想象,在这光明灿烂的年代,还有人出来做一些不道德也违法的工作。那个梅雨天,同我一起在远郊医院避雨的女人,她包口露出的药盒和手机屏幕上的消息泄露了她的身份。
我没有兴趣去研究她是什么心态,但调查到她正好有个弟弟,便以向社会曝光相要挟,让少年Y替我做了这件大事。她倒是至始至终不知道内情。
这公平正义吗?我当然也不觉得。其实我甚至认同清儿的观点,流产无异于谋杀,手术其实很残酷,然而一想到她痛苦的童年与青春,我不能不怀疑我这样想是否错了。
“少年啊,活在世间,谁的身上不背负着一些罪孽呢?我说我是天灾,是想你好受些,你非要当我是人祸,那我就是吧。”我没再多回复,直接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时代更替,文明日益发达,世界到底是变光明了,还是更黑暗了?这个问题困已经扰着我很久了。但为了所爱的人,在这明暗之间,总要永恒地挣扎下去啊。